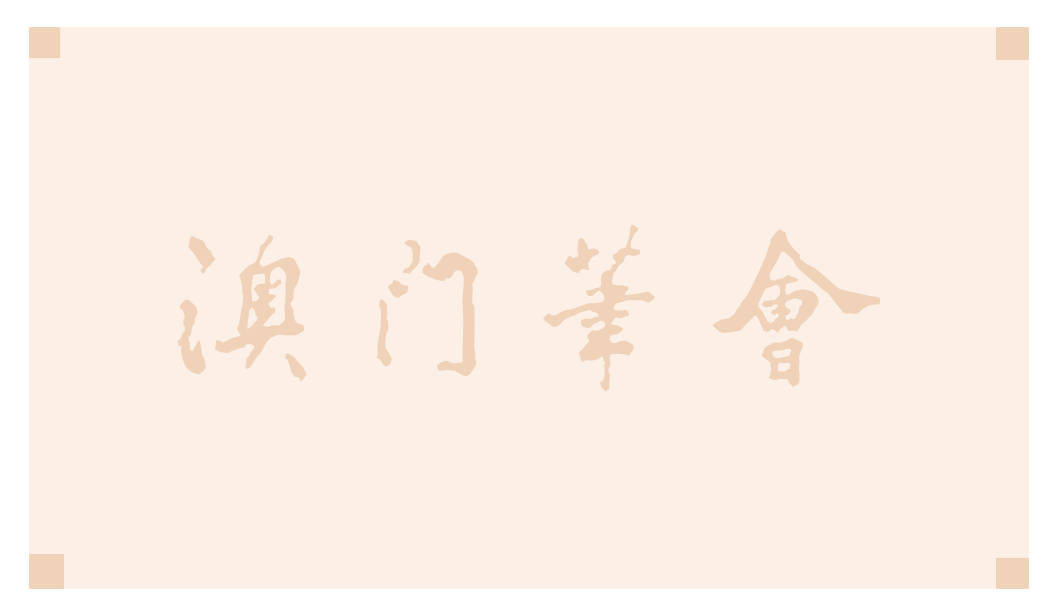〈華士古達嘉馬花園〉
華士古達嘉馬是葡萄牙著名航海家,曾開拓從歐洲繞好望角到印度的新航路,促進了歐亞貿易的發展,也開啟了葡萄牙對亞洲國家的殖民活動。這座花園是澳葡時期歷史的一個印證,作為其核心部分,達嘉馬銅像及基座上刻劃的三桅船、羅盤、金錨和海浪等浮雕,本質上是葡國歷史文化在澳門的藝術物化。一連串的文化符號,融入著名史詩《葡國魂》的詩意想像,在頌揚達嘉馬航海精神和業績的同時,藝術地或史詩般地實現了殖民合法性的建構。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六年來,這種澳葡時期遺存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已經並正在被現實生活重構,而〈華士古達嘉馬花園〉,正是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一種“現實認同與歷史記憶”的對話。
〈華士古達嘉馬花園〉這首詩,語言充滿隱喻、暗示和斷裂感,通過複雜意象和獨特句法傳達深沉隱秘的情感和思考,顯得晦澀難讀。不過也並非無“跡”可尋,其詩前“小引”便是進入此詩的門徑。詩人引用《說文解字》道:“取,捕捉也。从又从耳。”這就透露了一個信息:詩人之作此詩,乃因在“花園”中有所“捕捉”、有所收穫之致。
把握住“捕捉”這一關鍵詞,再進一步追問。其對象和方法,可以很快在詩中找到答案:原來詩人是用“耳朵捕捉流動的線條”。這句詩有些費解,其實是巧妙地運用了“通感”,將一種感官的感受,轉移至另一種感官上了。“線條”係指銅像基座浮雕上,海浪的條紋,本是靜態的視覺形象,而在詩人的想像中,這些水的“紋路”,竟“緩緩組合”,“像一條巨型銀魚不平坦的鱗片,此起又彼伏”,流動起來,激盪起來,“相互撞擊”起來,成為一種強烈的聽覺形象。
通感在本質上是“主觀情感的投射”,詩人“見波紋而聞水聲”的感官跨界連接,突破了常規思維,而與其對時光流逝、歷史變遷的感慨暗合。如是,銅像“大座”竟成為“上升的島嶼”,成為“出發的線索”,成為海洋征服和殖民的不斷延伸,就連距航海大發現遙遙六十年的“十字門”佔領,也牽連其中了。
詩的最後,寫詩人“捕捉”後的“發現”:一切都只是一個“循環”。就像俗話說的,從哪兒來的到哪兒去,輝煌一時的海上大發現、大擴張,如“太陽沉沒”,而“吞沒”它的,恰是那“無邊的”、“又快又慢”、“偶爾崎嶇”的“線條”匯成的“巨型銀魚”——歷史浪潮。時間悠悠,只遺留下來一尊“青銅色首級”循着身下的“線條”,“聆聽來時的路”。這裡的歸結,仍是以“聽”寫“視”。
〈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與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
讀此詩,第一眼看到的竟是兩個迂曲拗口的音譯街名。“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就是新馬路,“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就是荷蘭園大馬路,詩人有意用業已陌生的譯名而不用眾所熟知的俗稱,一下子領起讀者對街上曾經流通的不同語言文字狀況的思考,並在兩種稱謂的比較陳說中,感到一種歷史的沉重感和文化的多元性。這種“陌生化”手法,自然而有效地把城市過往與現今連接起來,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詩歌書寫和閱讀的“引子”。
循着這個“引子”進入詩行,迎面撲來的便是詩人對小城街道的情感投射:“Almeida,Almeida/我輕輕呼喚你的名字/就像你給我的迴響/聲音逐漸減去/微弱的混合……”——“Almeida”,對“亞美打利庇盧”來說是簡稱,對“肥利喇亞美打”來說則是代稱,而對兩條“大馬路”來說又成為昵稱,化繁為簡,語一言三,多麼親切、多麼私密、又多麼豐贍!輕輕的“呼喚”與微弱的“迴響”,混成出詩歌溫柔而深沉的基調。
於是讀者看見詩人起伏的情感裡纏繞着的散碎意象,以及由這些意象鏈接的記憶中的街道肌理:老舊、燃燒的“鋼鐡”,消失在空氣的“火”和“光”,暗示着街區景象由熱烈到消逝的虛無;路邊“採集光和塵埃”的“福建茶”、“朱蕉”和“細葉榕”,它們“萎縮又生長”,“裂紋蔓延又修補”的風貌,則隱喻着街道生命力的頑強和堅韌。兩組不同意象的並置,將街道高光時刻的閃耀與尋常圖景的綿延,組接成大馬路真實而獨特的質性鏡像。
值得注意的是,詩人記憶裡的街道情景方位,竟如此這般的具體而確定:“由前往後數,左邊第五排。”——這裡空間的精準定位,不僅大大增了“個體記憶”的真實感和可信度,而且讓“人”與“街”的共情共生,有了實在的落腳點。那“左邊第五排”的所在,並非簡單的空間位置,而是人生經歷和體悟的載體,裡面積蓄着沉甸甸情感的重量,是永遠不能,也無法遺忘的,那一聲“ 親愛的,我一直想成為你”,便是詩人甘願“自我消解”,以換取街道記憶長存的直陳。
或許是愛之過深的緣故吧,詩人居然又擔心起來:“不曾想過失去你”,其實就是始終害怕遺忘了“你”。因為面對歷史變遷和時代發展,記憶裡的真實往往具有某種脆弱性,無論它是“輕薄”“透明”的,還是“無可無不可的”,是“絶對的”,還是“虛幻的”,都會“像果實離開它的樹”一樣離去。這裡,表面上寫的是記憶的脆弱易逝,骨子裡發掘的卻是情感的堅定和深厚,可謂“曲折盡意”。
饒有深意的是,詩人在確認“果實離開樹”的必然之後,對“別離”一語的詞性解讀。他先是做理性分析:“分別,詞性動詞,準及物動詞,隸屬九十度”,試圖以抽象邏輯把控情緒,紓緩感性痛苦,然而辦不到;又做感性解讀:“別,詞性副詞,否定副詞”,從“別”的多個義項裡單挑出表示“不要”的詞性,從主觀任性的“選擇”中,透露生命反抗的天性。“不要/不要離開”——這迹近吶喊的反覆陳說,正是詩人在“別離”時,於理性和感性的糾結中,流瀉出來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真性情,詩說“別離是一個美妙的詞彙”;究其原因,乃在於這種性情對於“別離”的深度理解,其實“美妙”稱賞的並非“別離”本身,而是其中蘊含着的耐人尋味的生命體驗。
詩人最後寫道:“美麗的同義詞是擁擠”,這是詩中所有意象的疊加和全部情感的匯集,以此歸結全篇,可謂言簡意賅。句中的“美麗”和“擁擠”,都不是詞典裡標準而板滯的“原義”,而是詩歌語境中鮮活的“生成”,其歧義匯通的結果,實現了陌生而又令人驚喜的詩意傳達。詩人以敏銳的感知和獨出的聯想,將物理空間的密集,轉化為心理空間豐富多彩的存在,其間隱藏着述說不盡的人街共情共生的“美麗”。惟其如此,詩人的深情“呼喚”,也就“不再需要你的迴響”——大馬路上,每一個細節及其引起的每一道情感波瀾,都早已融入生命肌理,成為一種內在的永恆,“你”和你的“迴響”已經與“我”一體同在。這種以“不需要”表現深層多面“擁有”的抒寫,確乎是詩歌抵抗時間的一種動人的方式。
〈情人街和戀愛巷〉
讀這首詩,我首先注意到甘遠來寫下的“題記”:“最後他站起來,去到海邊,在那裡徘徊,心神錯亂。”這幾句引自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文字,是解讀此詩的鑰匙。引文所述,乃希臘聯軍主將阿喀琉斯在親密戰友帕特洛克羅斯犧牲後的痛苦情狀。這種痛苦,徘徊的腳步難以丈量它的長度,錯亂的心神無法承載它的重量,那是一種自幼形影不離、雙生並進的伙伴突然“離去”的精神撕裂,一種從生死考驗中淬煉出來的“深度共生關係”被摧毀時的靈魂顫抖。誠如阿喀琉斯的悲鳴慘嘆:失去帕特洛克羅斯,就是“失去我的另一半”,讓“我成了殘缺的人”。正是從這裡,遠來找到了宏大史詩敍述與現代愛情抒寫的“共情點”和“共通處”,即人對“完整”生命的追求和渴望,從而拉近了二者之間的時空距離,實現了史詩激情在狹窄的“戀愛巷”裡的詩意轉換。
追求“完整”,勢必珍視美好事物,與之難分難捨。生命痛苦的一個主因即是“美好”的亡失。阿喀琉斯海邊徘徊時的“心神錯亂”,與戀愛巷裡情侶“心臟”如“風爐鼓動”,就其本質而言都與“亡失”息息相關,只不過前者是“已然失去”的結果,而後者則是“唯恐失去”的憂慮罷了。正所謂“愛之愈深,慮之愈甚”,詩人擔心失去“愛情”的憂慮,“剪不斷、理還亂”,糾結為戀愛巷中一連串難以化解的心理矛盾。試看:“懸浮在半空的樹枝搖動/敲擊如銅”——“樹枝”的“懸浮”和“搖動”,暗示着所愛的無所依託和不確定性,而“銅”的鏗鏘“敲擊”,又隱喻着追求的堅定和執着,兩個意象對舉,於視覺與聽覺的巨大反差中,揭示出戀愛背後藏着的強烈衝突。
“你頭輕輕擱在我肩,氣流/衝擊牙齒的背面/高頻率的發音使我們始終試探”——“頭”與“肩”的溫暖觸碰,竟伴隨“氣流”衝擊牙齒的喘息和克制;急欲表述衷情的“高頻率發音”的熱切中,竟裹挾着不斷“試探”的小心翼翼,連串細節刻劃的是人在戀愛中“欲言又止”、“欲進又退”的矛盾心理,這也正是因“深度珍視”而“唯恐失之”者的生動具體情態。
“如何開始,如何終結/難離難捨的猶豫/像一個又一個黏連的元音”——詩人在兩個設問句後的“自答”,顯示出很高的文字技巧。其有意利用詞義矛盾來搭配詞語,造成了出奇制勝的效果。他以“難離難捨”的纏綿和堅韌,作為定語規限“猶豫”,讓這個表示“拿不定主意”的詞語也有了“確定性”,成為“如何”“不失去”的反覆思索。而將“元音”這個語音學專用詞語化為意象,用以作為比喻“猶豫”這一抽象概念的喻體,更見新意獨出。“元音”響亮而易延長的語音特點,決定了其特別適合抒情,比如將a和i兩個元音拼接,就合成了情人一諾千金的“愛ai”,而詩人竟將元音“一個一個黏連”起來,其間需要多少情感投入啊!
“風爐裡,心臟鼓動着/產生強烈的、嘈雜的聲音”——“風爐”的意象是“戀愛巷”的隱喻,詩人的筆觸未涉其外,而直抵其“裡”,揭示的那種巷間矛盾生命不可抑止的“鼓動”,及其洶湧的“熱烈”和“嘈雜”,恰與其外在的封閉、褊狹形成“外靜內動”的張力,從而由一個特別的角度,呈現出戀愛巷的本真樣貌。詩的歸結如此簡潔,可謂一“語”破題,一“象”見義。
李觀鼎
註:甘遠來《澳門街頭組曲(組詩)》,包括〈華士古達嘉馬花園〉、〈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與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和〈情人街和戀愛巷〉三首。
2025.09.17 澳門日報 第C08版:鏡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