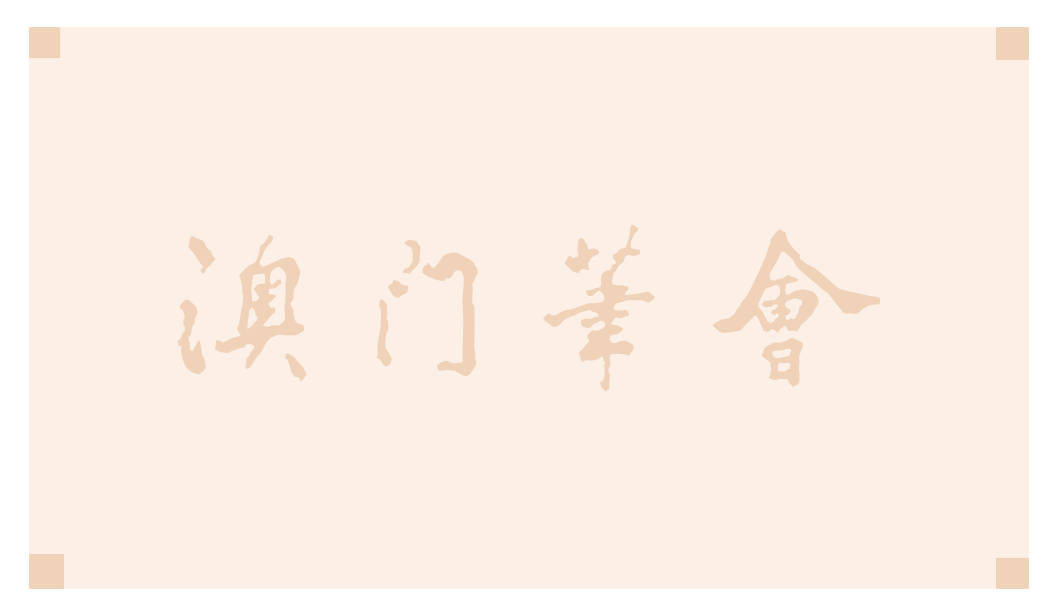〈华士古达嘉马花园〉
华士古达嘉马是葡萄牙着名航海家,曾开拓从欧洲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新航路,促进了欧亚贸易的发展,也开启了葡萄牙对亚洲国家的殖民活动。这座花园是澳葡时期歷史的一个印证,作为其核心部分,达嘉马铜像及基座上刻划的三桅船、罗盘、金锚和海浪等浮雕,本质上是葡国歷史文化在澳门的艺术物化。一连串的文化符号,融入着名史诗《葡国魂》的诗意想像,在颂扬达嘉马航海精神和业绩的同时,艺术地或史诗般地实现了殖民合法性的建构。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六年来,这种澳葡时期遗存所承载的歷史记忆已经并正在被现实生活重构,而〈华士古达嘉马花园〉,正是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种“现实认同与歷史记忆”的对话。
〈华士古达嘉马花园〉这首诗,语言充满隐喻、暗示和断裂感,通过复杂意象和独特句法传达深沉隐秘的情感和思考,显得晦涩难读。不过也并非无“迹”可寻,其诗前“小引”便是进入此诗的门径。诗人引用《说文解字》道:“取,捕捉也。从又从耳。”这就透露了一个信息:诗人之作此诗,乃因在“花园”中有所“捕捉”、有所收穫之致。
把握住“捕捉”这一关键词,再进一步追问。其对象和方法,可以很快在诗中找到答案:原来诗人是用“耳朵捕捉流动的线条”。这句诗有些费解,其实是巧妙地运用了“通感”,将一种感官的感受,转移至另一种感官上了。“线条”系指铜像基座浮雕上,海浪的条纹,本是静态的视觉形象,而在诗人的想像中,这些水的“纹路”,竟“缓缓组合”,“像一条巨型银鱼不平坦的鳞片,此起又彼伏”,流动起来,激盪起来,“相互撞击”起来,成为一种强烈的听觉形象。
通感在本质上是“主观情感的投射”,诗人“见波纹而闻水声”的感官跨界连接,突破了常规思维,而与其对时光流逝、歷史变迁的感慨暗合。如是,铜像“大座”竟成为“上升的岛屿”,成为“出发的线索”,成为海洋征服和殖民的不断延伸,就连距航海大发现遥遥六十年的“十字门”佔领,也牵连其中了。
诗的最後,写诗人“捕捉”後的“发现”:一切都只是一个“循环”。就像俗话说的,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辉煌一时的海上大发现、大扩张,如“太阳沉没”,而“吞没”它的,恰是那“无边的”、“又快又慢”、“偶尔崎岖”的“线条”汇成的“巨型银鱼”——歷史浪潮。时间悠悠,只遗留下来一尊“青铜色首级”循着身下的“线条”,“聆听来时的路”。这裡的归结,仍是以“听”写“视”。
〈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与肥利喇亚美打大马路〉
读此诗,第一眼看到的竟是两个迂曲拗口的音译街名。“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就是新马路,“肥利喇亚美打大马路”就是荷兰园大马路,诗人有意用业已陌生的译名而不用众所熟知的俗称,一下子领起读者对街上曾经流通的不同语言文字状况的思考,并在两种称谓的比较陈说中,感到一种歷史的沉重感和文化的多元性。这种“陌生化”手法,自然而有效地把城市过往与现今连接起来,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诗歌书写和阅读的“引子”。
循着这个“引子”进入诗行,迎面扑来的便是诗人对小城街道的情感投射:“Almeida,Almeida/我轻轻呼唤你的名字/就像你给我的迴响/声音逐渐减去/微弱的混合……”——“Almeida”,对“亚美打利庇卢”来说是简称,对“肥利喇亚美打”来说则是代称,而对两条“大马路”来说又成为昵称,化繁为简,语一言三,多么亲切、多么私密、又多么丰赡!轻轻的“呼唤”与微弱的“迴响”,混成出诗歌温柔而深沉的基调。
于是读者看见诗人起伏的情感裡缠绕着的散碎意象,以及由这些意象链接的记忆中的街道肌理:老旧、燃烧的“钢鐡”,消失在空气的“火”和“光”,暗示着街区景象由热烈到消逝的虚无;路边“採集光和尘埃”的“福建茶”、“朱蕉”和“细叶榕”,它们“萎缩又生长”,“裂纹蔓延又修补”的风貌,则隐喻着街道生命力的顽强和坚韧。两组不同意象的并置,将街道高光时刻的闪耀与寻常图景的绵延,组接成大马路真实而独特的质性镜像。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记忆裡的街道情景方位,竟如此这般的具体而确定:“由前往後数,左边第五排。”——这裡空间的精準定位,不仅大大增了“个体记忆”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而且让“人”与“街”的共情共生,有了实在的落腳点。那“左边第五排”的所在,并非简单的空间位置,而是人生经歷和体悟的载体,裡面积蓄着沉甸甸情感的重量,是永远不能,也无法遗忘的,那一声“ 亲爱的,我一直想成为你”,便是诗人甘愿“自我消解”,以换取街道记忆长存的直陈。
或许是爱之过深的缘故吧,诗人居然又担心起来:“不曾想过失去你”,其实就是始终害怕遗忘了“你”。因为面对歷史变迁和时代发展,记忆裡的真实往往具有某种脆弱性,无论它是“轻薄”“透明”的,还是“无可无不可的”,是“絶对的”,还是“虚幻的”,都会“像果实离开它的树”一样离去。这裡,表面上写的是记忆的脆弱易逝,骨子裡发掘的却是情感的坚定和深厚,可谓“曲折盡意”。
饶有深意的是,诗人在确认“果实离开树”的必然之後,对“别离”一语的词性解读。他先是做理性分析:“分别,词性动词,準及物动词,隶属九十度”,试图以抽象逻辑把控情绪,纾缓感性痛苦,然而办不到;又做感性解读:“别,词性副词,否定副词”,从“别”的多个义项裡单挑出表示“不要”的词性,从主观任性的“选择”中,透露生命反抗的天性。“不要/不要离开”——这迹近吶喊的反覆陈说,正是诗人在“别离”时,于理性和感性的纠结中,流泻出来的“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真性情,诗说“别离是一个美妙的词汇”;究其原因,乃在于这种性情对于“别离”的深度理解,其实“美妙”称赏的并非“别离”本身,而是其中蕴含着的耐人寻味的生命体验。
诗人最後写道:“美丽的同义词是拥挤”,这是诗中所有意象的疊加和全部情感的汇集,以此归结全篇,可谓言简意赅。句中的“美丽”和“拥挤”,都不是词典裡标準而板滞的“原义”,而是诗歌语境中鲜活的“生成”,其歧义汇通的结果,实现了陌生而又令人惊喜的诗意传达。诗人以敏锐的感知和独出的联想,将物理空间的密集,转化为心理空间丰富多彩的存在,其间隐藏着述说不盡的人街共情共生的“美丽”。惟其如此,诗人的深情“呼唤”,也就“不再需要你的迴响”——大马路上,每一个细节及其引起的每一道情感波澜,都早已融入生命肌理,成为一种内在的永恆,“你”和你的“迴响”已经与“我”一体同在。这种以“不需要”表现深层多面“拥有”的抒写,确乎是诗歌抵抗时间的一种动人的方式。
〈情人街和恋爱巷〉
读这首诗,我首先注意到甘远来写下的“题记”:“最後他站起来,去到海边,在那裡徘徊,心神错乱。”这几句引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文字,是解读此诗的钥匙。引文所述,乃希腊联军主将阿喀琉斯在亲密战友帕特洛克罗斯牺牲後的痛苦情状。这种痛苦,徘徊的腳步难以丈量它的长度,错乱的心神无法承载它的重量,那是一种自幼形影不离、双生并进的伙伴突然“离去”的精神撕裂,一种从生死考验中淬炼出来的“深度共生关系”被摧毁时的灵魂颤抖。诚如阿喀琉斯的悲鸣惨嘆:失去帕特洛克罗斯,就是“失去我的另一半”,让“我成了残缺的人”。正是从这裡,远来找到了宏大史诗敍述与现代爱情抒写的“共情点”和“共通处”,即人对“完整”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从而拉近了二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实现了史诗激情在狭窄的“恋爱巷”裡的诗意转换。
追求“完整”,势必珍视美好事物,与之难分难捨。生命痛苦的一个主因即是“美好”的亡失。阿喀琉斯海边徘徊时的“心神错乱”,与恋爱巷裡情侣“心脏”如“风炉鼓动”,就其本质而言都与“亡失”息息相关,只不过前者是“已然失去”的结果,而後者则是“唯恐失去”的忧虑罢了。正所谓“爱之愈深,虑之愈甚”,诗人担心失去“爱情”的忧虑,“剪不断、理还乱”,纠结为恋爱巷中一连串难以化解的心理矛盾。试看:“悬浮在半空的树枝摇动/敲击如铜”——“树枝”的“悬浮”和“摇动”,暗示着所爱的无所依託和不确定性,而“铜”的铿锵“敲击”,又隐喻着追求的坚定和执着,两个意象对举,于视觉与听觉的巨大反差中,揭示出恋爱背後藏着的强烈冲突。
“你头轻轻搁在我肩,气流/冲击牙齿的背面/高频率的发音使我们始终试探”——“头”与“肩”的温暖触碰,竟伴随“气流”冲击牙齿的喘息和克制;急欲表述衷情的“高频率发音”的热切中,竟裹挟着不断“试探”的小心翼翼,连串细节刻划的是人在恋爱中“欲言又止”、“欲进又退”的矛盾心理,这也正是因“深度珍视”而“唯恐失之”者的生动具体情态。
“如何开始,如何终结/难离难捨的犹豫/像一个又一个黏连的元音”——诗人在两个设问句後的“自答”,显示出很高的文字技巧。其有意利用词义矛盾来搭配词语,造成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他以“难离难捨”的缠绵和坚韧,作为定语规限“犹豫”,让这个表示“拿不定主意”的词语也有了“确定性”,成为“如何”“不失去”的反覆思索。而将“元音”这个语音学专用词语化为意象,用以作为比喻“犹豫”这一抽象概念的喻体,更见新意独出。“元音”响亮而易延长的语音特点,决定了其特别适合抒情,比如将a和i两个元音拼接,就合成了情人一诺千金的“爱ai”,而诗人竟将元音“一个一个黏连”起来,其间需要多少情感投入啊!
“风炉裡,心脏鼓动着/产生强烈的、嘈杂的声音”——“风炉”的意象是“恋爱巷”的隐喻,诗人的笔触未涉其外,而直抵其“裡”,揭示的那种巷间矛盾生命不可抑止的“鼓动”,及其汹湧的“热烈”和“嘈杂”,恰与其外在的封闭、褊狭形成“外静内动”的张力,从而由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出恋爱巷的本真样貌。诗的归结如此简洁,可谓一“语”破题,一“象”见义。
李观鼎
註:甘远来《澳门街头组曲(组诗)》,包括〈华士古达嘉马花园〉、〈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与肥利喇亚美打大马路〉和〈情人街和恋爱巷〉三首。
2025.09.17 澳门日报 第C08版: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