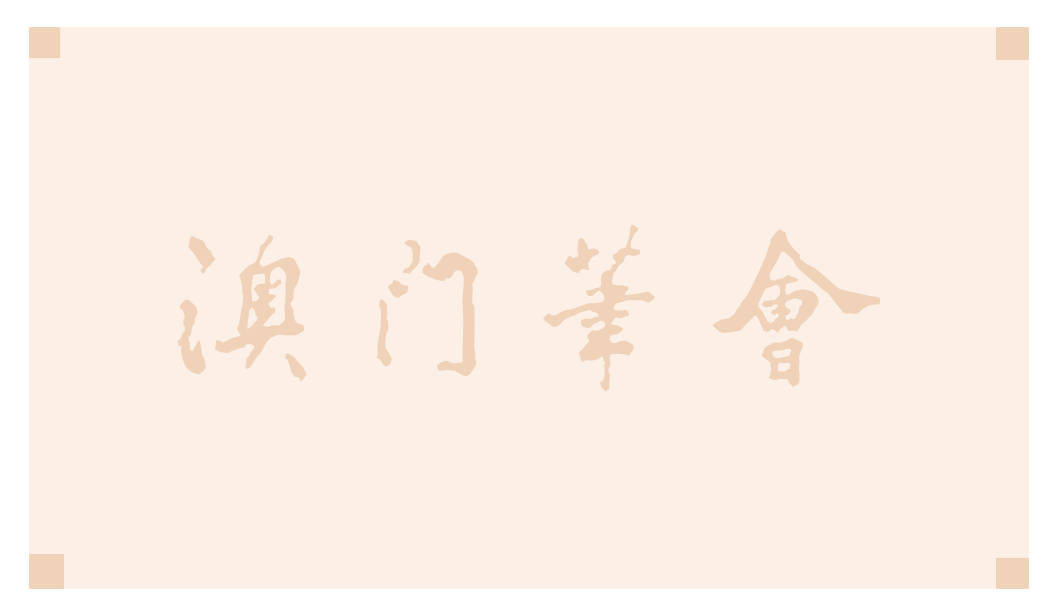聽山 作者:龔剛
宣紙上的淡墨化為雲煙 重演三千年浮沉 諸神退隱 奧林匹斯山水土不服 辛波斯卡說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於不寫詩的荒謬 她就是那個土地測量員 在有很多門的城堡前不得其門而入 他們聽到了歧義重重的語言 所以放棄傾聽 風止於馬鞍 巴別塔的廢墟上 關押着被放逐的聲音 天地在凝望中退縮為一塊岩石 寂靜如雨
首先,詩的題目運用了通感,沒有使用“看”對客觀實物“山”這一直觀感受,而是選擇了聽覺感官,拓展詩的維度空間。整體詩在內容上,巧妙用典,不僅僅是豐富了詩的內涵。聲成文,謂之音,可以借此去欣賞詩中典故所組成的旋律,張弛有度,為詩賦予了音樂之美,渲染了詩的表達。從深度廣度展開想像,整首詩立體化,提高閱讀體驗,詩更具活力。山巔石頭,不說話,但是見證歷史,也歷經滄桑,風雨磨礪,它總是靜靜地傾聽。曾經的一切皆藏於心不在焉的雲層,其實並未藏匿,透過被風吹皺雲層,詩人聽到了,感覺到了那漸遠的馬蹄聲、嘈雜聲,又漸漸地隱沒在歷史長河中,隱沒於山巔雲層,不曾看見,但可感知。只有石靜靜傾聽,此處大量留白,回味悠長。
追隨詩人,打開畫卷,一片雲煙籠罩,彷彿一切趨於平靜,但似乎難掩山雨欲來,風雲變幻。
雲開篇,止於石,緊扣畫面,展開想像宣紙上的水墨畫,隨着畫面推進,彷彿看到了熙熙攘攘的希臘眾神,熱鬧非凡,卻又瞬間隱去,讓繁榮的奧林匹斯山一時感到寂寞,似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辛波斯卡的詩,如若奔放旋律之後,紓緩的小提琴獨奏,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於不寫詩的荒謬,一切歸於平靜。
卡夫卡城堡,將畫面再一次推進,曾經遠去的,在變幻中輪迴……
安靜平和開始,以寂靜回應,前後呼應,猶如驚濤駭浪之後的平靜,呼應着辛波斯卡的詩,聽着並思考着,悲而不發,從容淡定。
所有的風平浪靜時,突然發現雲依然是那片雲,山依然是那座山,那塊岩石,寂靜孤獨,沒有人認識它,沒有名字。
漸漸地,這一切又漸漸隱去,一切歸於平靜,畫面回到起始,似乎合上了一部書。眼前還是翻滾的雲層,及偶爾透出雲端的那一方山石,靜靜地矗立於山巔,歷經千年,任憑風起雲湧,悠然矗立,詩回到了起始,收尾自然,依然留白,彷彿繪畫的留白,令人深思,永恆?天際,雲彩,岩石,前見古人,後見來者……
整首詩,猶如一座高山矗立於雲層之外,俯瞰着多維度空間,最後落點在我們凡人可見的一方岩石之上。詩起於雲煙,止於岩石,觀世間多少風雲變幻,只在你不曾在意的瞬間。無論是深度與廣度,都極富哲理,叙述點到為止,即興之時,又戛然而止,留白處,令人深思,極具語言張力。詩中典故,跨越時空,選材廣泛,需要一定的閱覽基礎,細品方能體會其中奧妙。
澳門日報 2025.09.10 第C08版:鏡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