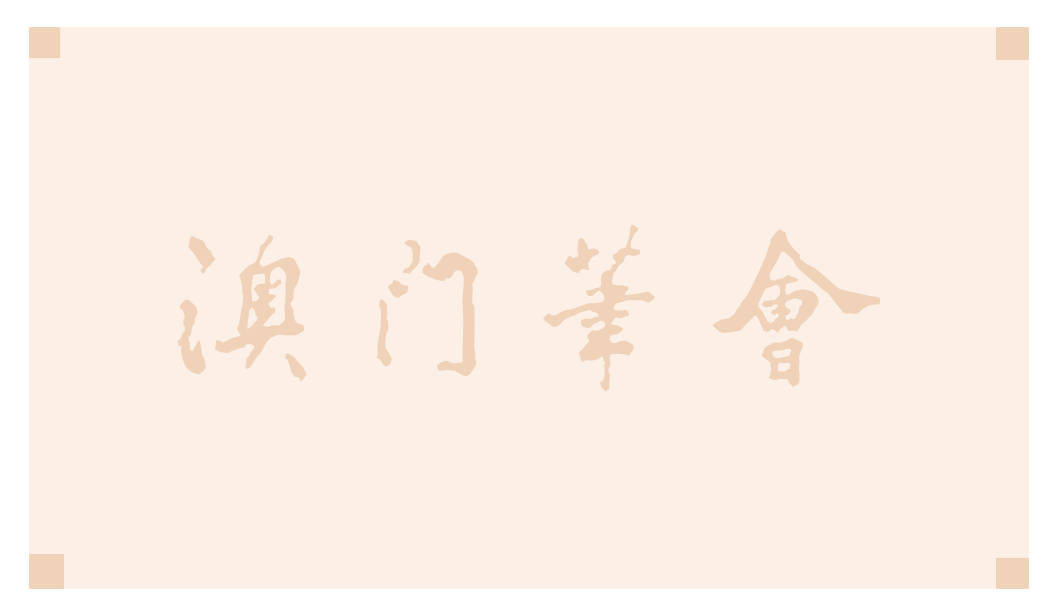听山 作者:龚刚
宣纸上的淡墨化为云烟 重演三千年浮沉 诸神退隐 奥林匹斯山水土不服 辛波斯卡说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她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 在有很多门的城堡前不得其门而入 他们听到了歧义重重的语言 所以放弃倾听 风止于马鞍 巴别塔的废墟上 关押着被放逐的声音 天地在凝望中退缩为一块岩石 寂静如雨
首先,诗的题目运用了通感,没有使用“看”对客观实物“山”这一直观感受,而是选择了听觉感官,拓展诗的维度空间。整体诗在内容上,巧妙用典,不仅仅是丰富了诗的内涵。声成文,谓之音,可以借此去欣赏诗中典故所组成的旋律,张弛有度,为诗赋予了音乐之美,渲染了诗的表达。从深度广度展开想像,整首诗立体化,提高阅读体验,诗更具活力。山巅石头,不说话,但是见证歷史,也歷经沧桑,风雨磨砺,它总是静静地倾听。曾经的一切皆藏于心不在焉的云层,其实并未藏匿,透过被风吹皱云层,诗人听到了,感觉到了那渐远的马蹄声、嘈杂声,又渐渐地隐没在歷史长河中,隐没于山巅云层,不曾看见,但可感知。只有石静静倾听,此处大量留白,回味悠长。
追随诗人,打开画卷,一片云烟笼罩,彷彿一切趋于平静,但似乎难掩山雨欲来,风云变幻。
云开篇,止于石,紧扣画面,展开想像宣纸上的水墨画,随着画面推进,彷彿看到了熙熙攘攘的希腊众神,热鬧非凡,却又瞬间隐去,让繁荣的奥林匹斯山一时感到寂寞,似乎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辛波斯卡的诗,如若奔放旋律之後,纾缓的小提琴独奏,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一切归于平静。
卡夫卡城堡,将画面再一次推进,曾经远去的,在变幻中轮迴……
安静平和开始,以寂静回应,前後呼应,犹如惊涛骇浪之後的平静,呼应着辛波斯卡的诗,听着并思考着,悲而不发,从容淡定。
所有的风平浪静时,突然发现云依然是那片云,山依然是那座山,那块岩石,寂静孤独,没有人认识它,没有名字。
渐渐地,这一切又渐渐隐去,一切归于平静,画面回到起始,似乎合上了一部书。眼前还是翻滚的云层,及偶尔透出云端的那一方山石,静静地矗立于山巅,歷经千年,任凭风起云湧,悠然矗立,诗回到了起始,收尾自然,依然留白,彷彿绘画的留白,令人深思,永恆?天际,云彩,岩石,前见古人,後见来者……
整首诗,犹如一座高山矗立于云层之外,俯瞰着多维度空间,最後落点在我们凡人可见的一方岩石之上。诗起于云烟,止于岩石,观世间多少风云变幻,只在你不曾在意的瞬间。无论是深度与广度,都极富哲理,叙述点到为止,即兴之时,又戛然而止,留白处,令人深思,极具语言张力。诗中典故,跨越时空,选材广泛,需要一定的阅览基础,细品方能体会其中奥妙。
澳门日报 2025.09.10 第C08版: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