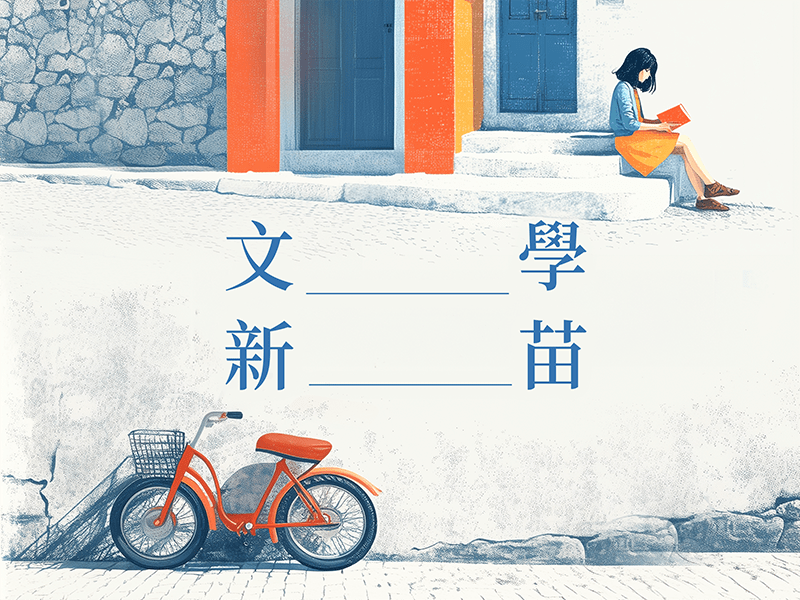窗外鳥鳴響起,溫暖的陽光透過玻璃切 入視綫,眼前漫開一片蜂蜜色的黃,是艷陽 天。放學的鐘聲剛響起尾音,我背起書包走 向回家的必經之路。
正無聊地踢著石子時,忽然有油香劈面 撞來,那香氣是活的,像條金燦燦的綢帶, 一頭拴著油鍋,一頭纏住我的鼻尖。循著味 道望去,一根根金黃色的油條躺在油鍋裏, 等待著人們來將它們買走。店主阿姨抄著長 筷子輕點油條表面,“嗞——”地一聲,表皮 立刻綻開裂紋,露出裡頭雪白的絮狀肌理。 這場景太熟悉了。我鬼使神差摸出硬幣,金 屬被手心捂得發燙,準備將這個闖進我生 活的“不速之客”買走。不知是否因有陽光 的濾鏡,平時不起眼的一家小油條店,今天 炸出來的油條卻格外金黃,讓人忍不住嘗 上一口。
油條是我小時候最愛的“零食”,親切 的店長阿姨看我流口水的樣子,二話不説便 端來一碟油條。咬下去的瞬間,酥脆的咔嚓 聲在齒間炸開,油香混著碱水味湧上顎間。 好吃,但總覺得少了什麽,像一首忘了最後 一句的童謠。
記憶突然倒帶。七歲那年回福建老家, 老屋的磚墻被曬出鹽霜。唯一一次回鄉,卻 讓我深深地記住了這個地方,是一個有爺 爺的味道的地方。福建的景色我已經不記 得了,只記得烈日,和爺爺做的油條。
那也是一個艷陽天,在外面玩了一整天 的我筋疲力盡地回到家,摔傷了膝蓋卻硬撐 著不哭。是爺爺第一個發現我褲管上洇開 的血漬,就像朵鏽紅色小花。他蹲下時,後 頸曬脫的皮翹起透明三角,掌心粗糲得像 砂紙,擦藥時卻輕得像羽毛。“給你炸根油 條?”爺爺的聲音還是這樣溫柔,不等回答 就起身往灶台走,舊拖鞋啪嗒啪嗒拍打著 夯土地面。
爺爺的油條在鎮上出名。麵團在他手里 三抻兩轉就變成長條,入油時“唰”地激起 油浪。我趴在灶台邊數油泡,看它們從芝麻 大長到黃豆大,最後“啵”地破滅在油面。剛 出鍋的油條燙得拿不住,爺爺便撕成小段吹 氣:“慢點吃,燙破天堂要喝三天粥咧!”他 總把“上顎”說成“天堂”。那天的油條格外 香。脆皮下藏著綿軟的內里,鹹裡透著一絲 甜,像陽光曬透麥穗的味道。後來才明白, 特殊的不是手藝,是他撕油條時總把最蓬松 的芯留給我,是他佝僂著背往灶膛添柴火, 火光把白髮染成暖橘色。
那獨特的味道我沒再感受過第二遍,許是 那次的油條有爺爺的陪伴,許是有爺爺的愛, 我也拿不準,但我清晰地知道,那是我和爺爺 之間的味道。只可惜爺爺現在的身體狀況每 況愈下,想要再次吃到那個味道,恐怕很難。 回過神來,鳥兒還在不停叫喚,阿姨的 油條店也人多了起來。不是很大的店面,卻 裝了很多客人,卻裝不下我龐雜的回憶。霓 虹的招牌還在閃著,天色漸漸暗下來,阿姨 正把最後一根油條裝袋,油紙滲出圓圓的油 漬,遞給門口穿草莓裙的小女孩。女孩踮腳 去夠,髮繩上的塑料珠子晃啊晃。
我忽然不遺憾了。有些味道本就不能被 複製,就像爺爺炸油條時灶膛裡噼啪作響的 火星,永遠亮在我記憶的暗處。回家的路上, 暮色把電線桿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像一根 放涼的油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