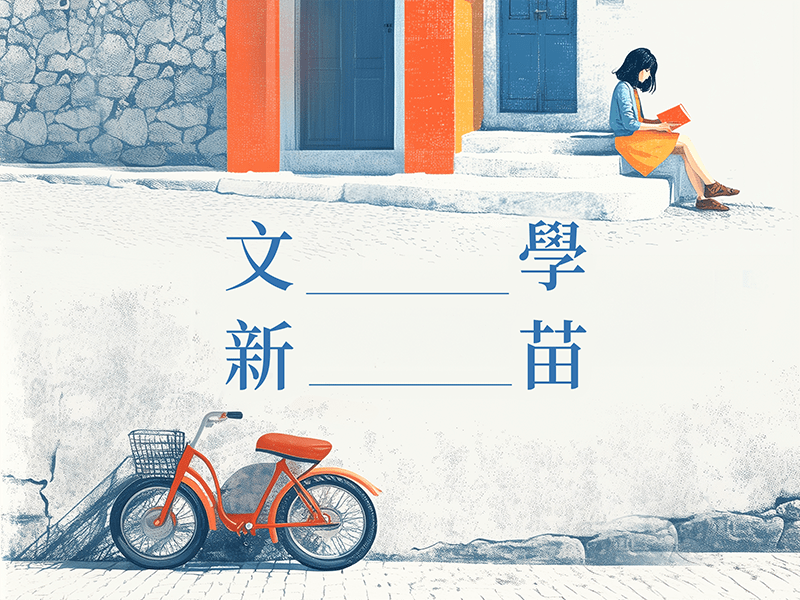小引
文學是什麼?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給文學下定義,除了審美這一維度,還涉及社會、心理、文化等多種因素,不同時代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歸結。諸如:
關注詞語、意象如何表達的“符號學”,認為文學是“符號系統的編碼遊戲”;
關注語言如何創新的“語言學”,認為文學是“語言的陌生化運用系統”;
關注如何講好故事的“敘事學”,認為文學是“故事的講述邏輯”;
關注讀者如何參與及其生成意義的“接受美學”認為,文學是“讀者與文本的對話”;
關注“結構模式如何潛藏的“結構主義”,認為文學是“深層結構的模式化表達”(如英雄故事的常規模式:啟程、冒險、歸來);
關注作家潛意識欲望及其隱喻表達的“精神分析學”,認為文學是“潛意識的象徵投射”(如卡夫卡《變形記》中格里高爾變成的甲蟲);
關注作品中自然與人類關係,反對破壞生態,倡導可持續理論的“生態批評”,認為文學是“自然與文明的對話”……真是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我們似乎已經習慣於這樣的認知:“文學是一種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和手段,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感情和審美理想的藝術形式。”而上述這些“界定”,各說各理,亦各擁其理;獨闢蹊徑,自成一派,又共同形成了對文學質性的多元指向。對此,文學習作者不可不察也。
但這要慢慢來。我這裡僅根據澳門青年文學營推動文學創作的需要,參照各種觀點,提出幾個命題與大家討論,以期觸摸文學的本真。
“文學是人學。”
這是俄國著名作家高爾基,就文學本質對文學下的定義。它深刻揭示了文學與人的緊密關係,言簡意賅,切中肯綮,自1931年在《談技藝》﹙之二﹚中提出後,很快被社會廣泛認同,業已成為關於文學的經典論斷。篇幅所限,我在此且談兩點體會。
其一,“人”是文學表現的核心對象。作家的創作經驗和讀者的閱讀經驗告訴我們,文學歷來以寫人為旨趣,無論敘事、抒情、詠物還是科幻,實質上都是人的生存狀態、精神世界和生命意義的鏡象。
敘事作品,當然要講好故事,但“事在人為”,首要的是要寫好“人”,通過故事情節,把人物性格、情懷、境界展現出來。我們閱讀文學作品,本質上是讀人,讀故事裡的人物。所謂“什麼人做什麼事”,讀懂其人,才能讀懂其事。《三國演義》第五十回,講的是關羽在華容道義釋曹操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作者卻寫出了諸葛亮的“智”、曹操的“疑”、關羽的“義”。鮮明突出的人物性格,讓簡單的故事情節充盈並深刻起來。諸葛亮之智並非小聰明,而是大智慧:他料定曹操兵敗赤壁後必走華容道,這是戰術智慧;他明知關羽重義必放曹操,還要派其前去攔截,這是戰略智慧,因為“曹操不能死”是天下三分的大格局之需,曹操一死,鼎足之勢必將崩潰,於蜀漢極為不利;而關羽經此一事,亦將汲取教訓,徹底了斷與曹操“恩情”糾葛。曹操之疑,實際上是一種在大智慧面前的窘境和焦慮。他生性多疑且自負,被諸葛亮在華容小道故意放火生煙所誤導,竟認為煙火是“虛張聲勢”。疑必惑,惑而錯解,判斷就會失誤,過度的自信讓他終於陷入關羽的埋伏。關羽之義亦非小義,在“義釋”這件事上,那可是大於“忠”的。他接受任務前,先立軍令狀,這是對蜀國誓死效忠的承當。可是臨陣時“忠”與“義”竟發生強烈的矛盾衝突,最後義戰勝了忠,終於釀成大錯。試問:這回書離開了鮮活的人物性格,還有多少看頭?
現在一些年輕習作者熱衷於“編故事”,寫出來的東西往往有“事”而無“人”,這就讓故事的深度和新鮮度大打折扣。因為故事情節雖可以“編”出來,甚至可以“編”出精彩來,但是編多了總難免雷同或重複。比如寫愛情故事就有各種模式,什麼青梅竹馬式、一見鍾情式、英雄救美式、患難與共式、忠貞不渝式、喜新厭舊式等等,你選擇任何一種模式去編排鋪陳,都很難做到同框出新,因為早就讓前人寫盡、寫濫了。因此,當我們構思作品時,一定要提筆思“人”,好好想一想筆下的故事將怎樣呈現人物性格,或者說這個人物將以怎樣的個性進入故事,並推動故事的發展。
當然,以上談的只是傳統小說,現代小說弱化或淡化故事情節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也十分值得重視。較諸傳統小說,現代小說並不以事寫人、寫性格,而是以人本身的狀態寫人的生活。比如美國著名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當我們在談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寫一群人圍坐一起喝酒,聊着各自對愛情的理解和看法,其間充斥着關於“愛”的東拉西扯和胡言亂語。沒有什麼故事情節,也沒有典型人物,但寫的還是人,是現代感情生活中的大多數人,他們對“愛情是什麼”永遠說不清道不明。同樣是寫人,現代小說更着力於人的存在方式、內心世界及其與現實生活的關係。現代小說以其豐富的內容、創新的形式和技巧,與傳統小說形成了緊密的互補關係,它們共同推動着作為“人學”的文學之發展,並為這種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說到寫景狀物,從心理學角度看,其實就是從物象到表象再到意象的運動過程。所謂“物象”即自然景物;“表象”即以往保留在記憶中的客觀事物的映象;意象即藝術形象,如康德所說,“是一種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顯現”。在此過程中,創作者對客觀物象的感知和感動,喚起記憶中積累的表象,促其進入現場的感知範圍,並在藝術構思中進行加工改造,通過“有意想象”使之成為意象。其間,每一步都離不開“人”。究其本質,就是“客觀物象”在人的感知、記憶、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動推動下,被不斷地“主觀化”即“人化”。
了解了意象生成的過程,再來看寫景狀物作品,便不至於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了。比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杜甫《絶句》﹚——描寫的只是清新明麗的春日景色嗎?裡面還暗含着詩人經安史之亂,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暫時擺脫戰亂顛沛流離之苦的心境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蘇軾《題西林壁》﹚——亦非廬山“面目”的簡單描摹,那橫、側、遠、近、高、低的多角度透視,正是詩人經歷了“烏台詩案”和黃州流放的苦難,對起伏多變的人生的情感聚焦啊。“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早發白帝城》﹚——要知道長江三峽水流湍急,水下礁石散佈,詩人的江峽舟行充滿艱難險阻,然而其筆下的“景象”竟如此這般的輕快、暢順,以至於傳統語境中觸發悲涼、哀傷的“猿聲”,都成為一種歡快感動的樂音了。何耶?無他,這兩句詩寫的是詩人的“心境”,那是一種因罪流放夜郎而途中遇赦的大喜過望,一種歷經拘控、屈辱、折磨終於重獲自由的開豁釋懷。“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律詩首、頷、頸、尾四聯,講求起、承、轉、合關係,白詩這兩句頸聯,恰在全詩境界經營和情感傳達的轉捩點上。詩中侵染古道、漫延荒城的“晴翠”承上啟下,一方面將“燒不盡”、“吹又生”的原上草的無限生命力加以生動的具象化展現,一方面又為“送別”營造出蒼茫遼遠的氛圍,讓“萋萋別情”溢滿字裡行間。草的蓬勃生機與人的情感指向交融互見,自然風景便有了精神,而詩中的哲學意味也有了依托。文學作品所寫的景與物,乃是作者眼中、心中之“景”與“物”,必然浸染着人的情感和靈性;而情感的傳達,又不是空泛的言說,須常常附設於鮮活景物的畫面上。惟其如此,王國維做出這樣的歸結:“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再說說科幻作品,其本質仍然是寫“人”。這類作品雖然以科學元素為基礎,並借此對故事核心進行設定,但這種“設定”即便在無邊的宇宙或遙遠的未來,其虛構的異星時空場景,也與“人”的情感、困境、選擇和追求息息相關,探討的常常是倫理、文明、人性等社會生活的深層問題。例如劉慈欣的《三體》,其核心設計是“三體文明入侵”、“黑森林法則”、“降維打擊”等,表面上是再現一場宇宙級的科技對抗,而實際上是對處於極度壓力下的人類群體“人性”的拆解。又如安德魯.斯坦頓的《機器人總動員》,故事設定為“人類因環境污染而逃離地球,依靠AI維持生存的未來,其核心衝突看似“機器人互力拯救地球”,而實質卻是人類情感被科技“異化”之後如何“回歸”的敘事。這是通過“科技問題”,對“人”在現代社會喪失人的“本質”的可能之預警。
大量優秀作品表明,科幻小說作為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結構“骨架”都是“以人為魂”的,即便故事核心是科幻設定,箇中“人的情感和需求”,也須通過人物一次次“選擇”、一個個“細節”呈現出來。否則,主題被科技遮蔽,人物陷入“扁平化”,科幻寫作勢必偏離“人學”的中心。當然,“文學是人學”的要旨並不是一定要塑造“典型人物”或刻畫“複雜人物”,而是要探討人的“存在”意義。科幻作品也可以描寫“扁平人物”,但並非僅僅作為串連或推動故事情節的“工具”,只為完成“任務”而設,性格、心理始終處於“無變化”狀態,這樣寫來就不是“文學”,而成為單純的“科技+幻想”了。習作者一定要了解,科幻只是“殼”,人物才是“魂”,故事不能只講科技不講人,哪怕是“扁平人物”,最終也要回到“人性”,回到“人的情感、困境、選擇和追求。”
其二,文學的要義在於表現人性。所謂人性,是人類有生俱來的、共有的普遍本性特質,它貫穿並決定着人的行為方式、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具有“自利”與“利他”的複雜的矛盾性。文學以“人”為核心展開的敘事與抒情,其實就是一種反映人性的“鏡像”創造。從古希臘悲劇對命運與人性衝突的叩問,到現代小說對個體精神困境的剖析,無論題材、風格如何演變,對人性的描寫與表現始終是文學無法剝離的本質——它既是文學打動讀者的情感紐帶,也是文學承載社會思考、實現精神傳承的核心載體。
文學的魅力,本質上是“人的魅力”。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納與共情,往往始於對作品中人物人性的感知。當《紅樓夢》中林黛玉在落花時節葬花,其敏感、孤傲與對生命脆弱的共情,正是人性中“對美好事物的珍視”與“對自身命運的悲憫”的具像化;當《活着》中的福貴歷經親人離世、時代動盪卻仍選擇堅韌活着,其背後是人性中“求生本能”與“生命韌性”的真實寫照。這些描寫沒有停留在人物的身份、時代標簽上,而是深入到人類共通的情感與精神層面——無論是喜悅、痛苦、渴望還是掙扎,都能讓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讀者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從而產生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這種共鳴,正是文學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能夠長久觸動人心的關鍵所在。
文學從不只是“講故事的藝術”,更是“反思人的藝術”。通過對人性的深度挖掘,文學能夠將個體命運與社會現實、時代精神相連,進而傳遞對世界的思考。魯迅筆下的阿Q,其“精神勝利法”不僅是個體的性格缺䧟,更是對舊中國民眾麻木、愚昧人性的深刻批判,背後承載的是對民族精神覺醒的呼喚: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過安娜對愛情自由的追求與社會禮教的衝突,展現了人性中“欲望與道德”的博弈,折射出19世紀俄國社會的階級矛盾與思想變革。可以說,文學對社會的反思,往往不是通過直白的議論,而是通過對人性的細膩描寫——讓讀者在理解人物選擇的同時,自然而然地思考人性與社會、時代的關係,這種思考的深度與廣度,正是文學社會價值的核心體現。
人類文明的傳承,不僅是知識與技術的傳遞,更是精神與人性的延續。文學作為記錄人性的“精神檔案”,通過對不同時代人性的描寫,將人類共通的精神品質——如善良、勇敢、正義,以及對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傳。從《詩經》中“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所展現的人性溫情,到《百年孤獨》中布恩迪亞家族對“孤獨”與“救贖”的永恆探索;從《西遊記》中孫悟空“從叛逆到皈依”的人性成長,到《哈利.波特》中“愛能戰勝邪惡”的人性信念,這些作品所描寫的人性本質,早已超越了具體的時代與地域,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當後世讀者在這些作品中感受到人性的力量時,實際上是承接前人的精神遺產,而文學正是通過這種對人性的持續書寫,完成了人類精神的傳承與延續。
綜上,無論是構建情感共鳴、承載社會思考,還是實現精神傳承,文學的所有價值都離不開對人性的描寫與表現。人性不僅是文學的核心內容,更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所在——失去了對人性的關注,文學便失去了靈魂,也失去了打動人心、影響社會、傳承文明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