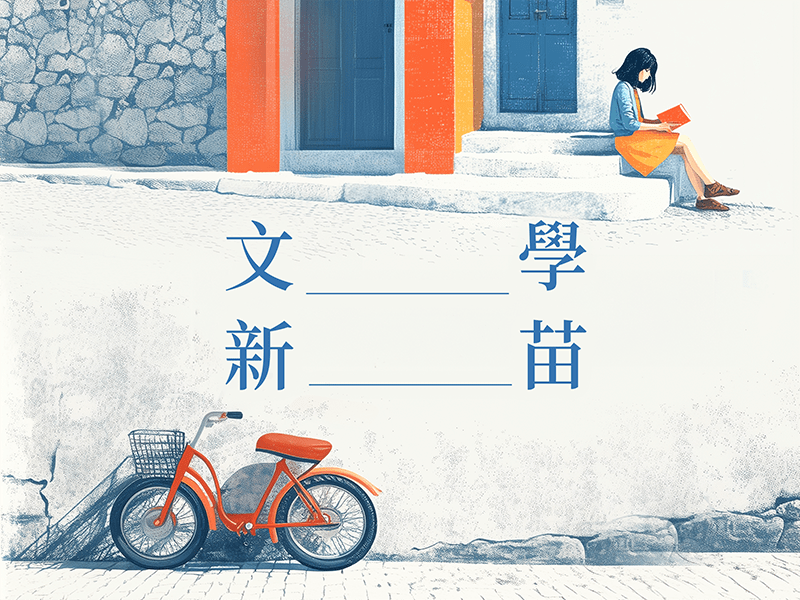窗外鸟鸣响起,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切 入视綫,眼前漫开一片蜂蜜色的黄,是艳阳 天。放学的钟声刚响起尾音,我背起书包走 向回家的必经之路。
正无聊地踢着石子时,忽然有油香噼面 撞来,那香气是活的,像条金灿灿的绸带, 一头拴着油锅,一头缠住我的鼻尖。循着味 道望去,一根根金黄色的油条躺在油锅裏, 等待着人们来将它们买走。店主阿姨抄着长 筷子轻点油条表面,“嗞——”地一声,表皮 立刻绽开裂纹,露出裡头雪白的絮状肌理。 这场景太熟悉了。我鬼使神差摸出硬币,金 属被手心捂得发烫,準备将这个闯进我生 活的“不速之客”买走。不知是否因有阳光 的滤镜,平时不起眼的一家小油条店,今天 炸出来的油条却格外金黄,让人忍不住尝 上一口。
油条是我小时候最爱的“零食”,亲切 的店长阿姨看我流口水的样子,二话不説便 端来一碟油条。咬下去的瞬间,酥脆的咔嚓 声在齿间炸开,油香混着碱水味湧上颚间。 好吃,但总觉得少了什麽,像一首忘了最後 一句的童谣。
记忆突然倒带。七岁那年回福建老家, 老屋的砖墻被晒出盐霜。唯一一次回乡,却 让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有爷 爷的味道的地方。福建的景色我已经不记 得了,只记得烈日,和爷爷做的油条。
那也是一个艳阳天,在外面玩了一整天 的我筋疲力盡地回到家,摔伤了膝盖却硬撑 着不哭。是爷爷第一个发现我裤管上洇开 的血渍,就像朵锈红色小花。他蹲下时,後 颈晒脱的皮翘起透明三角,掌心粗粝得像 砂纸,擦药时却轻得像羽毛。“给你炸根油 条?”爷爷的声音还是这样温柔,不等回答 就起身往灶台走,旧拖鞋啪嗒啪嗒拍打着 夯土地面。
爷爷的油条在镇上出名。麵团在他手里 三抻两转就变成长条,入油时“唰”地激起 油浪。我趴在灶台边数油泡,看它们从芝麻 大长到黄豆大,最後“啵”地破灭在油面。刚 出锅的油条烫得拿不住,爷爷便撕成小段吹 气:“慢点吃,烫破天堂要喝三天粥咧!”他 总把“上颚”说成“天堂”。那天的油条格外 香。脆皮下藏着绵软的内里,咸裡透着一丝 甜,像阳光晒透麦穗的味道。後来才明白, 特殊的不是手艺,是他撕油条时总把最蓬松 的芯留给我,是他佝偻着背往灶膛添柴火, 火光把白髮染成暖橘色。
那独特的味道我没再感受过第二遍,许是 那次的油条有爷爷的陪伴,许是有爷爷的爱, 我也拿不準,但我清晰地知道,那是我和爷爷 之间的味道。只可惜爷爷现在的身体状况每 况愈下,想要再次吃到那个味道,恐怕很难。 回过神来,鸟儿还在不停叫唤,阿姨的 油条店也人多了起来。不是很大的店面,却 装了很多客人,却装不下我庞杂的回忆。霓 虹的招牌还在闪着,天色渐渐暗下来,阿姨 正把最後一根油条装袋,油纸渗出圆圆的油 渍,递给门口穿草莓裙的小女孩。女孩踮腳 去够,髮绳上的塑料珠子晃啊晃。
我忽然不遗憾了。有些味道本就不能被 复製,就像爷爷炸油条时灶膛裡噼啪作响的 火星,永远亮在我记忆的暗处。回家的路上, 暮色把电线桿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 放凉的油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