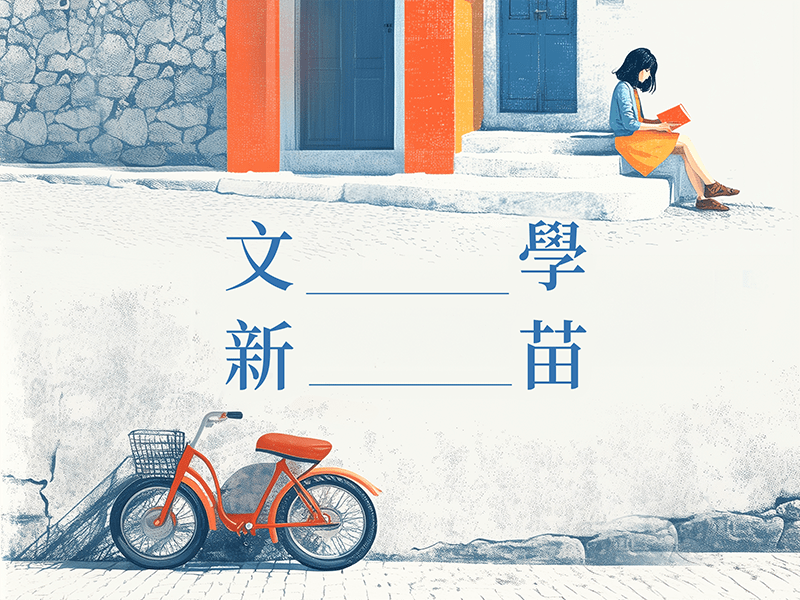小引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给文学下定义,除了审美这一维度,还涉及社会、心理、文化等多种因素,不同时代不同人站在不同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归结。诸如:
关注词语、意象如何表达的“符号学”,认为文学是“符号系统的编码游戏”;
关注语言如何创新的“语言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陌生化运用系统”;
关注如何讲好故事的“叙事学”,认为文学是“故事的讲述逻辑”;
关注读者如何参与及其生成意义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关注“结构模式如何潜藏的“结构主义”,认为文学是“深层结构的模式化表达”(如英雄故事的常规模式:启程、冒险、归来);
关注作家潜意识欲望及其隐喻表达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文学是“潜意识的象徵投射”(如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的甲虫);
关注作品中自然与人类关系,反对破坏生态,倡导可持续理论的“生态批评”,认为文学是“自然与文明的对话”……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认知:“文学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艺术形式。”而上述这些“界定”,各说各理,亦各拥其理;独闢蹊径,自成一派,又共同形成了对文学质性的多元指向。对此,文学习作者不可不察也。
但这要慢慢来。我这裡仅根据澳门青年文学营推动文学创作的需要,参照各种观点,提出几个命题与大家讨论,以期触摸文学的本真。
“文学是人学。”
这是俄国着名作家高尔基,就文学本质对文学下的定义。它深刻揭示了文学与人的紧密关系,言简意赅,切中肯綮,自1931年在《谈技艺》﹙之二﹚中提出後,很快被社会广泛认同,业已成为关于文学的经典论断。篇幅所限,我在此且谈两点体会。
其一,“人”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对象。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读者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文学歷来以写人为旨趣,无论叙事、抒情、咏物还是科幻,实质上都是人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的镜象。
叙事作品,当然要讲好故事,但“事在人为”,首要的是要写好“人”,通过故事情节,把人物性格、情怀、境界展现出来。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本质上是读人,读故事裡的人物。所谓“什么人做什么事”,读懂其人,才能读懂其事。《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讲的是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者却写出了诸葛亮的“智”、曹操的“疑”、关羽的“义”。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让简单的故事情节充盈并深刻起来。诸葛亮之智并非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他料定曹操兵败赤壁後必走华容道,这是战术智慧;他明知关羽重义必放曹操,还要派其前去拦截,这是战略智慧,因为“曹操不能死”是天下三分的大格局之需,曹操一死,鼎足之势必将崩溃,于蜀汉极为不利;而关羽经此一事,亦将汲取教训,彻底了断与曹操“恩情”纠葛。曹操之疑,实际上是一种在大智慧面前的窘境和焦虑。他生性多疑且自负,被诸葛亮在华容小道故意放火生烟所误导,竟认为烟火是“虚张声势”。疑必惑,惑而错解,判断就会失误,过度的自信让他终于陷入关羽的埋伏。关羽之义亦非小义,在“义释”这件事上,那可是大于“忠”的。他接受任务前,先立军令状,这是对蜀国誓死效忠的承当。可是临阵时“忠”与“义”竟发生强烈的矛盾冲突,最後义战胜了忠,终于酿成大错。试问:这回书离开了鲜活的人物性格,还有多少看头?
现在一些年轻习作者热衷于“编故事”,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有“事”而无“人”,这就让故事的深度和新鲜度大打折扣。因为故事情节虽可以“编”出来,甚至可以“编”出精彩来,但是编多了总难免雷同或重复。比如写爱情故事就有各种模式,什么青梅竹马式、一见钟情式、英雄救美式、患难与共式、忠贞不渝式、喜新厌旧式等等,你选择任何一种模式去编排铺陈,都很难做到同框出新,因为早就让前人写盡、写滥了。因此,当我们构思作品时,一定要提笔思“人”,好好想一想笔下的故事将怎样呈现人物性格,或者说这个人物将以怎样的个性进入故事,并推动故事的发展。
当然,以上谈的只是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弱化或淡化故事情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十分值得重视。较诸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并不以事写人、写性格,而是以人本身的状态写人的生活。比如美国着名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当我们在谈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写一群人围坐一起喝酒,聊着各自对爱情的理解和看法,其间充斥着关于“爱”的东拉西扯和胡言乱语。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也没有典型人物,但写的还是人,是现代感情生活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对“爱情是什么”永远说不清道不明。同样是写人,现代小说更着力于人的存在方式、内心世界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现代小说以其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和技巧,与传统小说形成了紧密的互补关系,它们共同推动着作为“人学”的文学之发展,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说到写景状物,从心理学角度看,其实就是从物象到表象再到意象的运动过程。所谓“物象”即自然景物;“表象”即以往保留在记忆中的客观事物的映象;意象即艺术形象,如康德所说,“是一种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显现”。在此过程中,创作者对客观物象的感知和感动,唤起记忆中积累的表象,促其进入现场的感知範围,并在艺术构思中进行加工改造,通过“有意想象”使之成为意象。其间,每一步都离不开“人”。究其本质,就是“客观物象”在人的感知、记忆、情感、想象等心理活动推动下,被不断地“主观化”即“人化”。
了解了意象生成的过程,再来看写景状物作品,便不至于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了。比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絶句》﹚——描写的只是清新明丽的春日景色吗?裡面还暗含着诗人经安史之乱,在成都浣花溪畔建成草堂,暂时摆脱战乱颠沛流离之苦的心境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亦非庐山“面目”的简单描摹,那横、侧、远、近、高、低的多角度透视,正是诗人经歷了“乌台诗案”和黄州流放的苦难,对起伏多变的人生的情感聚焦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早发白帝城》﹚——要知道长江三峡水流湍急,水下礁石散佈,诗人的江峡舟行充满艰难险阻,然而其笔下的“景象”竟如此这般的轻快、畅顺,以至于传统语境中触发悲凉、哀伤的“猿声”,都成为一种欢快感动的乐音了。何耶?无他,这两句诗写的是诗人的“心境”,那是一种因罪流放夜郎而途中遇赦的大喜过望,一种歷经拘控、屈辱、折磨终于重获自由的开豁释怀。“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律诗首、颔、颈、尾四联,讲求起、承、转、合关系,白诗这两句颈联,恰在全诗境界经营和情感传达的转捩点上。诗中侵染古道、漫延荒城的“晴翠”承上启下,一方面将“烧不盡”、“吹又生”的原上草的无限生命力加以生动的具象化展现,一方面又为“送别”营造出苍茫辽远的氛围,让“萋萋别情”溢满字裡行间。草的蓬勃生机与人的情感指向交融互见,自然风景便有了精神,而诗中的哲学意味也有了依托。文学作品所写的景与物,乃是作者眼中、心中之“景”与“物”,必然浸染着人的情感和灵性;而情感的传达,又不是空泛的言说,须常常附设于鲜活景物的画面上。惟其如此,王国维做出这样的归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再说说科幻作品,其本质仍然是写“人”。这类作品虽然以科学元素为基础,并借此对故事核心进行设定,但这种“设定”即便在无边的宇宙或遥远的未来,其虚构的异星时空场景,也与“人”的情感、困境、选择和追求息息相关,探讨的常常是伦理、文明、人性等社会生活的深层问题。例如刘慈欣的《三体》,其核心设计是“三体文明入侵”、“黑森林法则”、“降维打击”等,表面上是再现一场宇宙级的科技对抗,而实际上是对处于极度压力下的人类群体“人性”的拆解。又如安德鲁.斯坦顿的《机器人总动员》,故事设定为“人类因环境污染而逃离地球,依靠AI维持生存的未来,其核心冲突看似“机器人互力拯救地球”,而实质却是人类情感被科技“异化”之後如何“回归”的叙事。这是通过“科技问题”,对“人”在现代社会丧失人的“本质”的可能之预警。
大量优秀作品表明,科幻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结构“骨架”都是“以人为魂”的,即便故事核心是科幻设定,箇中“人的情感和需求”,也须通过人物一次次“选择”、一个个“细节”呈现出来。否则,主题被科技遮蔽,人物陷入“扁平化”,科幻写作势必偏离“人学”的中心。当然,“文学是人学”的要旨并不是一定要塑造“典型人物”或刻画“复杂人物”,而是要探讨人的“存在”意义。科幻作品也可以描写“扁平人物”,但并非仅仅作为串连或推动故事情节的“工具”,只为完成“任务”而设,性格、心理始终处于“无变化”状态,这样写来就不是“文学”,而成为单纯的“科技+幻想”了。习作者一定要了解,科幻只是“壳”,人物才是“魂”,故事不能只讲科技不讲人,哪怕是“扁平人物”,最终也要回到“人性”,回到“人的情感、困境、选择和追求。”
其二,文学的要义在于表现人性。所谓人性,是人类有生俱来的、共有的普遍本性特质,它贯穿并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具有“自利”与“利他”的复杂的矛盾性。文学以“人”为核心展开的叙事与抒情,其实就是一种反映人性的“镜像”创造。从古希腊悲剧对命运与人性冲突的叩问,到现代小说对个体精神困境的剖析,无论题材、风格如何演变,对人性的描写与表现始终是文学无法剥离的本质——它既是文学打动读者的情感纽带,也是文学承载社会思考、实现精神传承的核心载体。
文学的魅力,本质上是“人的魅力”。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纳与共情,往往始于对作品中人物人性的感知。当《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落花时节葬花,其敏感、孤傲与对生命脆弱的共情,正是人性中“对美好事物的珍视”与“对自身命运的悲悯”的具像化;当《活着》中的福贵歷经亲人离世、时代动盪却仍选择坚韧活着,其背後是人性中“求生本能”与“生命韧性”的真实写照。这些描写没有停留在人物的身份、时代标签上,而是深入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精神层面——无论是喜悦、痛苦、渴望还是挣扎,都能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读者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正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能够长久触动人心的关键所在。
文学从不只是“讲故事的艺术”,更是“反思人的艺术”。通过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文学能够将个体命运与社会现实、时代精神相连,进而传递对世界的思考。鲁迅笔下的阿Q,其“精神胜利法”不仅是个体的性格缺䧟,更是对旧中国民众麻木、愚昧人性的深刻批判,背後承载的是对民族精神觉醒的呼唤: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安娜对爱情自由的追求与社会礼教的冲突,展现了人性中“欲望与道德”的博弈,折射出19世纪俄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与思想变革。可以说,文学对社会的反思,往往不是通过直白的议论,而是通过对人性的细腻描写——让读者在理解人物选择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思考人性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这种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正是文学社会价值的核心体现。
人类文明的传承,不仅是知识与技术的传递,更是精神与人性的延续。文学作为记录人性的“精神档案”,通过对不同时代人性的描写,将人类共通的精神品质——如善良、勇敢、正义,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传。从《诗经》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展现的人性温情,到《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对“孤独”与“救赎”的永恆探索;从《西游记》中孙悟空“从叛逆到皈依”的人性成长,到《哈利.波特》中“爱能战胜邪恶”的人性信念,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性本质,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与地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当後世读者在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人性的力量时,实际上是承接前人的精神遗产,而文学正是通过这种对人性的持续书写,完成了人类精神的传承与延续。
综上,无论是构建情感共鸣、承载社会思考,还是实现精神传承,文学的所有价值都离不开对人性的描写与表现。人性不仅是文学的核心内容,更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所在——失去了对人性的关注,文学便失去了灵魂,也失去了打动人心、影响社会、传承文明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