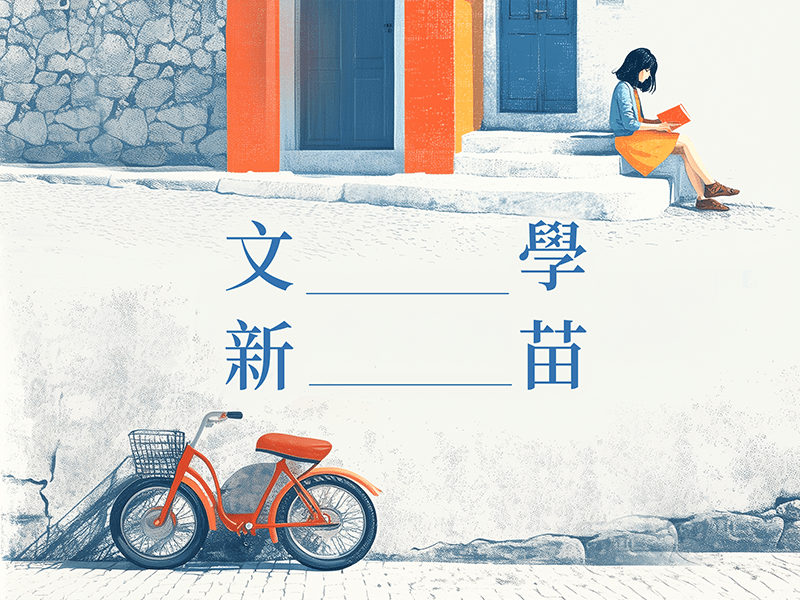无聊时观树,亦觉树无聊;低眉时观花,花亦会生悲。
学校裡B座直对的那棵常青树,歷经风雨飘摇後,仍矗立于校园一角。她坚如磐石,粗壮的树幹支撑着树冠往高处生长。随着年级和课室的变化,角度也变化。但无论怎看,树都无变化。我以为树已步入暮年,直到初三,她竟萌生了新叶。本来死板的一片绿色在边缘上新抹了一圈淡绿,绿得生机勃勃,与原有的绿铺排得既奇异又融洽。那是个寒气入骨的春天,可新叶不理会低温的警语肆意生长。我第一次觉得眼前的一切如油画般奢美。
这新意已经够可爱,可似乎未能得到青睐。另一处的花呢?
D座教学楼前的鱼池假山一景一直备受喜爱。几乎每个人经过,都会盛赞它的清丽。明媚的朝阳下能看到鱼池波光粼粼的水面,光柔美得像给眼前景套上了一层童话般的滤镜,似要带人荡入仙境。人们却指责後面的花,抢眼且艳俗。藤蔓携花一直绕着教学楼向上攀爬,叫人难以忽视她的存在感。在楼梯转角处抬头,能望见斜垂的花帘;在二楼走廊处眺望,能望见花制的瀑布。原是最浪漫的画面,可这颜色偏偏是品红。花也许听过很多锐评,但她不作声,只在寻常的春季裡演上一场易容术。也许她无意在他人的纸上留下一抹芳香,但也不碍总有人想将此製成当季限定的纪念邮票。我把花的新貌看作春的馈赠,打算为她留下几行散诗作为回礼。然而她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新颜,在无声中凋零。而今年初春不太冷,好像无人留意到这幕的凄美。
此时我又想起了那晚在澳门塔旁回家的路上,遍地都是木棉花的尸体,“尸臭”湧入鼻中。被木棉花砸中的剎那,我才发现它是有重量的。现实感带来的冲击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了现实。原来我早已忘却我是这样活在现实中的一个切切实实存在的人。于是我开始期待花落。天生对环境感知过于笨拙导致我经常被落叶、花瓣砸中。一般人被不知何物砸中,都是懊恼地叹气,可我见到砸中我的是已经衰败但亦曾绽放过的生命时,心情便一下子爽朗了起来。如果你能想像这样一个画面,你定能体会到我的快乐。然而这只是我荒唐、迷离的精神世界中的一角。
树为何再生新叶,花为何重塑容颜,我们无从得知。事实上,我们也不该深究。我们习惯了抱着融情于景、寄情于物的心理看待植物,把不属于它们的情感强加在它们身上,可曾想过这种中国文学常见的移情手法太失礼?植物与我们完全不一致,或许它们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由这种把主观思想包裹着客观事物,再加以想像和情感,这种思维方式真的能爆发般创造出古诗词裡绮丽华美的意象吗?
可谁能直视到意象本身呢?在把季节和景象带来的思绪存放在植物身上的那刻,我又把自己抽离了出来。我想试着不带我的主观情感去解读它们,看清我们身处的世界。植物朝颜夕改,只是气候无常罢了。也许比起各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更应看到它们本真的美。
学校的景,其实不足一两处精彩。在走廊往下探出头的藤蔓,枝蔓与建筑光影的交织,莫名在空中盘旋的羽毛和永生的羽毛球花,各有各的魅力。就连排球场旁那棵最大的树,也有它的美妙。摇摇欲坠的絮条和枝上聚居的麻雀有着不错的意境。尤其是雨後,若能透过地上的积水看到它的倒影,那定是一幅绝画。说到树,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校外每棵树有着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枯黄、鲜绿、浅青,交织在一起,定是春的手笔吧!否则夏和秋冬能有如此多颜色?那么我要期待每一个季节了。想到这裡,我竟然会开始期待生活了。再细看,对面停车场层的花和叶每一丛都是不同的颜色。风在托起它们的舞姿时,有发现每一处都风采各异吗?
不论如何,花瓣徐徐飘落的季节已然降临,耳边的歌正在迴旋。在不可逆的季节流转中,愿你我能看见真实的美好,沐浴在清凉的日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