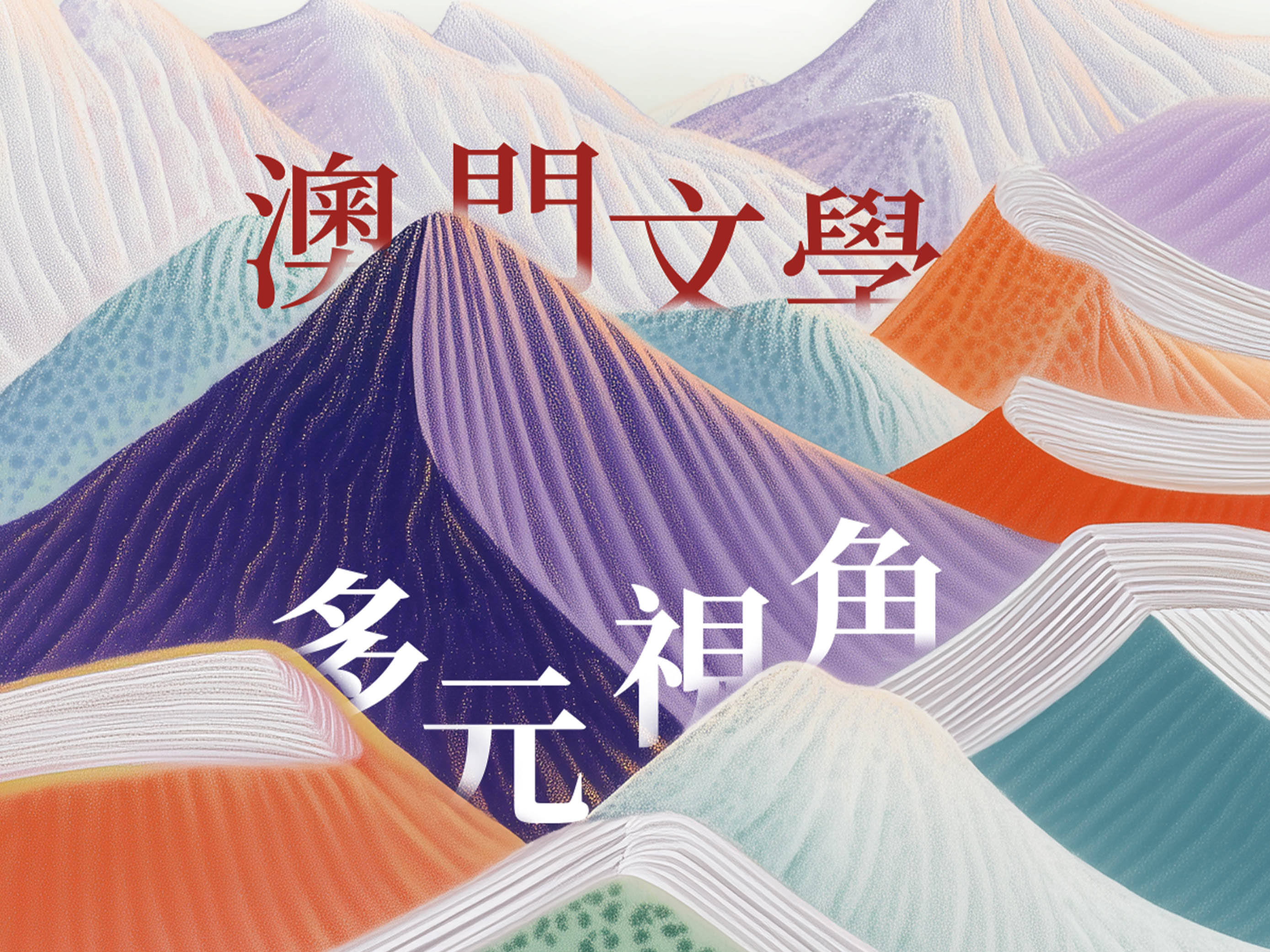《父親》,第四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散文組推薦獎,作者雙口。
人生如戲,戲如行人生。《父親》通過揭示「戲院帶位員」的父親一生,映照出歷人類社會共存的世代鴻溝。
在充滿張力的情節中,父子之情並非傳統敘事中溫馨和諧的典範,也非朱自清《背影》中單純的誤解與衝突,而是在缺席與存在、誤解與理解、怨恨與愧疚之間不斷震盪的複雜情感。作者通過戲院空間的隱喻、光影符號的對比,以及貫穿生命週期的記憶碎片,建構出一段既疏離又緊密、既矛盾又和諧的親情關係:
一、缺席的父親與永恆的等待
父親的職業特性決定了這段父子情的先天殘缺。戲院作為「沒有時間」的異質空間,「帶位員」的職業符號吞噬了父親日常該有的形態。在孩童的視角中,生日蛋糕上融化的蠟燭、冷卻的肥雞,成為時間流逝的殘酷刻度。那句未說出口的「好好陪我」的願望,與牛郎織女的傳說形成殘忍對照——不是銀河阻隔,而是被戲院黑幕切割的平行時空。
這種「父職缺席」的冰冷感在「椅座夾人事件」中得到了緩解:當兒子被困在機械結構的縫隙中,父親的拯救行動具有雙重救贖意義。螺絲刀拆解的不僅是物理困境,更是長期缺席累積的情感冰層。黑暗中那雙突然出現的手,既是被迫中斷工作的職業本能,也是潛意識中父愛的本能噴發。這個戲劇性場景成為父子關係的隱喻:父親總在危機時刻現身,卻在平淡日常中隱形,如同戲院燈光般明滅不定。
二、職業認同與情感代價的悖論
父親對戲院的執著,實質上顛覆了傳統父子倫理。當「帶位員」的身份壓倒「父親」角色,這種職業狂熱在兒子眼中既是背叛也是謎題。文中反覆出現的問題——「難道對暗淡前景還存期望?」、「與戲院有何內幕?」——暴露出兒子試圖用功利主義邏輯解讀父親的徒勞。這種代際認知鴻溝,本質上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衝突:父親將戲院視為精神聖殿,兒子卻只看到「路邊石子」般的社會地位。
更具悲劇性的是,這種職業認同通過血緣關係形成情感傳導。當兒子「假愛這地方」卻不自覺模仿父親改造家居時,戲院已成為基因密碼般的家族牌坊。那些精心布置的立體聲喇叭與電影海報,既是對父親的致敬,也是對自我童年缺失的補償儀式。這種矛盾心理揭示出親情的宿命性:我們終將在抗拒中成為父母的鏡像。
三、疾病敘事中的角色逆轉
癌症的降臨徹底顛覆了父子權力結構。當父親從「永動機般的帶位員」退化為「比黑洞更黑洞的存在」,兒子被迫從被照料者轉變為照護者。文中對病體的描述極具衝擊力:「每一片肉均是口」的意象,將生理痛苦轉化為對存在意義的詰問。此時的戲院隱喻發生質變:曾經給予父親生命力的空間,如今成為加速其消亡的對照組——正如癌細胞的增殖與菲林齒孔的磨損形成殘酷的互文。
但疾病也意外地成為和解契機。當兒子似乎用謊言建構戲院復甦的幻象,父親「精神奕奕地回應」的場景,暴露出血緣關係中最深層的默契:用善意的虛構維持彼此的存在感。這種角色扮演式的對話,如同戲院中虛實交錯的光影,在死亡陰影下反而顯現出親情最純粹的本質——不需要真相,只需要精神和心靈上的互動。
四、羞恥感與認同焦慮的雙重變奏
本章中段潛藏著強烈的階級敘事。同學父親們的「經理、公務員、老闆」身份,與帶位員的職業落差,構成兒子成長過程中的精神創傷。這種「難堪」不僅是孩童虛榮心的投射,更是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觀的強勢植入。當父親在戲院中「安排所有觀眾位置」,卻在社會階梯上被永久固定於底層,這種權力位置的悖論加深了代際矛盾。
隨著生命經驗的累積,羞恥感逐漸轉化為存在主義式的覺悟。兒子最終意識到,父親用五十年堅守的並非某個職業,而是對抗虛無的精神姿態。那些曾經令人難堪的「帶位動作」,在時光濾鏡下顯現出熱愛工作的神聖。
五、記憶中的情感考古
文中不斷閃現的記憶碎片,構成父子關係的另類編年史。從「被卸下的椅座」到「改造的家居戲院」,這些物質痕跡成為情感考古的關鍵證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溫暖記憶幾乎都發生在戲院空間內部:黑暗中緊握的手、耳畔的低語、菲林轉動的細響。這暗示著父愛的獨特性——它必須依附於某種超越日常的儀式空間才能顯現。
這種記憶建構方式暴露出現代親情的本質困境:我們對父母的認知,不容易在他們的職業身份與家庭角色之間取得平衡。在文末,當作者承認「我才真正發現我所說的,並不是一個親人的經歷,而是一個生命永遠的執著」時,有了實質的覺醒:父愛的存在需超出傳統倫理框架,在更廣闊的維度中被理解。
當戲院終將被數位洪流吞沒,父親的執著顯現出先知般的悲劇性。這對父子的故事,既是個體命運的縮影,也是世代精神困境的寓言。那些被重複了五十年的帶位動作,那些在黑暗中悄然傳遞的體溫,最終在記憶的銀幕上融合為存在主義的堅定回應:愛的本質,或許就是允許對方成為自己命運的偏執狂。當兒子最終接過父親的手電筒,在人工製造的黑暗裡重現帶位儀式時,這種跨越生死的角色扮演,成就了父子間最動人的情感救贖——我們終究要用父母的邏輯,才能讀懂他們愛的密碼。
在我看來,這是一個有著淒美背景的溫情故事。「更深愁對月,憐此薄命人」這句崑曲唱詞的點題,似乎過於悲涼!父親的戲院人生猶如本雅明筆下的「靈光」殘片,在數位時代的暗夜中閃爍微光。當我們理解這種「重複即永恆」的存在智慧,方能真正讀懂文末的終極隱喻:那些被父親「吻遍的菲林」,實為機械時代最動人的情書——用五十年的時光長度,在齒孔間鐫刻永恆的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