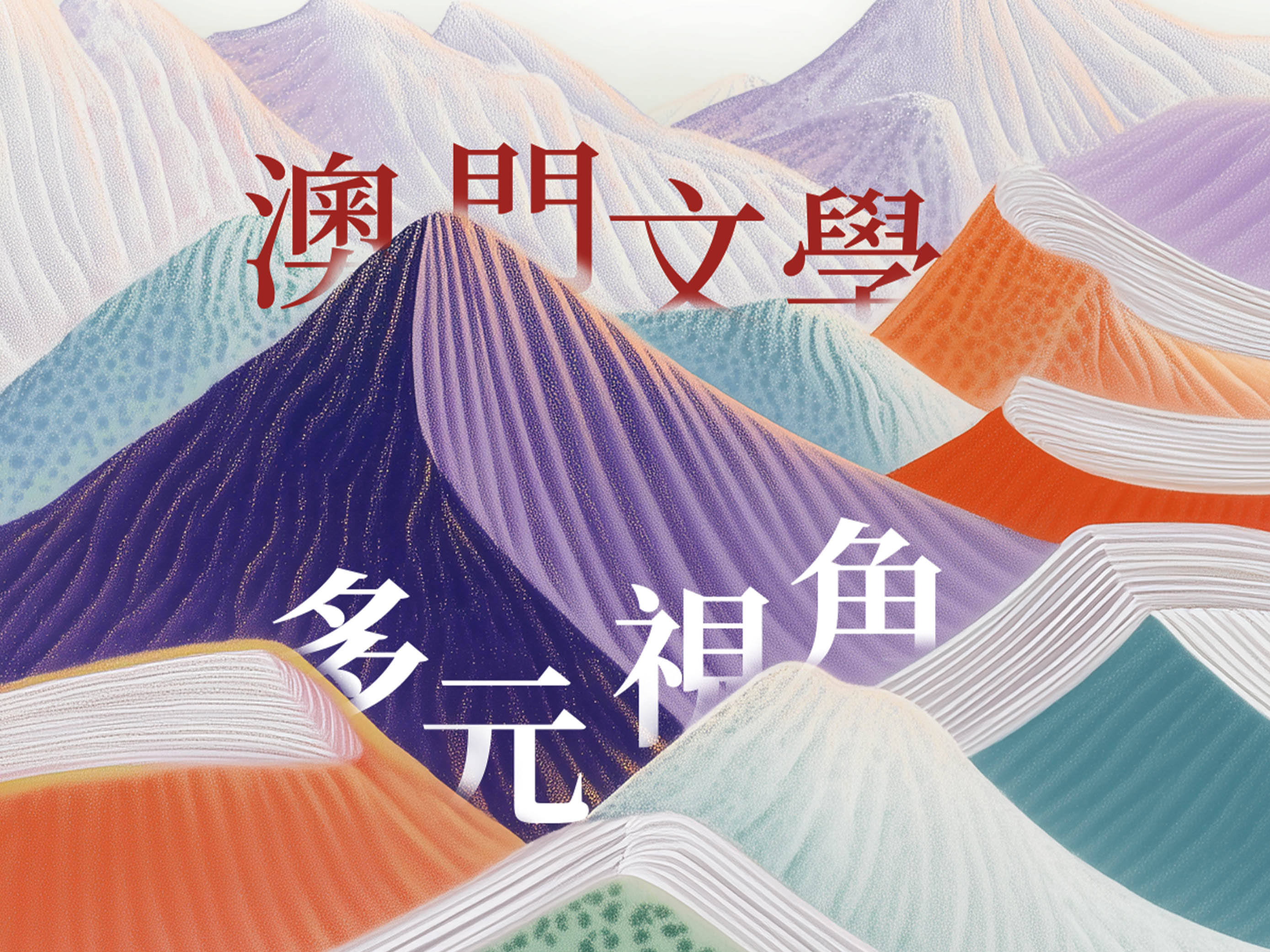《父亲》,第四届纪念李鹏翥文学奖散文组推荐奖,作者双口。
人生如戏,戏如行人生。《父亲》通过揭示「戏院带位员」的父亲一生,映照出歷人类社会共存的世代鸿沟。
在充满张力的情节中,父子之情并非传统叙事中温馨和谐的典範,也非朱自清《背影》中单纯的误解与冲突,而是在缺席与存在、误解与理解、怨恨与愧疚之间不断震盪的复杂情感。作者通过戏院空间的隐喻、光影符号的对比,以及贯穿生命週期的记忆碎片,建构出一段既疏离又紧密、既矛盾又和谐的亲情关系:
一、缺席的父亲与永恆的等待
父亲的职业特性决定了这段父子情的先天残缺。戏院作为「没有时间」的异质空间,「带位员」的职业符号吞噬了父亲日常该有的形态。在孩童的视角中,生日蛋糕上融化的蜡烛、冷却的肥鸡,成为时间流逝的残酷刻度。那句未说出口的「好好陪我」的愿望,与牛郎织女的传说形成残忍对照——不是银河阻隔,而是被戏院黑幕切割的平行时空。
这种「父职缺席」的冰冷感在「椅座夹人事件」中得到了缓解:当儿子被困在机械结构的缝隙中,父亲的拯救行动具有双重救赎意义。螺丝刀拆解的不仅是物理困境,更是长期缺席累积的情感冰层。黑暗中那双突然出现的手,既是被迫中断工作的职业本能,也是潜意识中父爱的本能喷发。这个戏剧性场景成为父子关系的隐喻:父亲总在危机时刻现身,却在平淡日常中隐形,如同戏院灯光般明灭不定。
二、职业认同与情感代价的悖论
父亲对戏院的执着,实质上颠覆了传统父子伦理。当「带位员」的身份压倒「父亲」角色,这种职业狂热在儿子眼中既是背叛也是谜题。文中反覆出现的问题——「难道对暗淡前景还存期望?」、「与戏院有何内幕?」——暴露出儿子试图用功利主义逻辑解读父亲的徒劳。这种代际认知鸿沟,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父亲将戏院视为精神圣殿,儿子却只看到「路边石子」般的社会地位。
更具悲剧性的是,这种职业认同通过血缘关系形成情感传导。当儿子「假爱这地方」却不自觉模仿父亲改造家居时,戏院已成为基因密码般的家族牌坊。那些精心布置的立体声喇叭与电影海报,既是对父亲的致敬,也是对自我童年缺失的补偿仪式。这种矛盾心理揭示出亲情的宿命性:我们终将在抗拒中成为父母的镜像。
三、疾病叙事中的角色逆转
癌症的降临彻底颠覆了父子权力结构。当父亲从「永动机般的带位员」退化为「比黑洞更黑洞的存在」,儿子被迫从被照料者转变为照护者。文中对病体的描述极具冲击力:「每一片肉均是口」的意象,将生理痛苦转化为对存在意义的诘问。此时的戏院隐喻发生质变:曾经给予父亲生命力的空间,如今成为加速其消亡的对照组——正如癌细胞的增殖与菲林齿孔的磨损形成残酷的互文。
但疾病也意外地成为和解契机。当儿子似乎用谎言建构戏院復甦的幻象,父亲「精神奕奕地回应」的场景,暴露出血缘关系中最深层的默契:用善意的虚构维持彼此的存在感。这种角色扮演式的对话,如同戏院中虚实交错的光影,在死亡阴影下反而显现出亲情最纯粹的本质——不需要真相,只需要精神和心灵上的互动。
四、羞耻感与认同焦虑的双重变奏
本章中段潜藏着强烈的阶级叙事。同学父亲们的「经理、公务员、老闆」身份,与带位员的职业落差,构成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创伤。这种「难堪」不仅是孩童虚荣心的投射,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强势植入。当父亲在戏院中「安排所有观众位置」,却在社会阶梯上被永久固定于底层,这种权力位置的悖论加深了代际矛盾。
随着生命经验的累积,羞耻感逐渐转化为存在主义式的觉悟。儿子最终意识到,父亲用五十年坚守的并非某个职业,而是对抗虚无的精神姿态。那些曾经令人难堪的「带位动作」,在时光滤镜下显现出热爱工作的神圣。
五、记忆中的情感考古
文中不断闪现的记忆碎片,构成父子关系的另类编年史。从「被卸下的椅座」到「改造的家居戏院」,这些物质痕迹成为情感考古的关键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温暖记忆几乎都发生在戏院空间内部:黑暗中紧握的手、耳畔的低语、菲林转动的细响。这暗示着父爱的独特性——它必须依附于某种超越日常的仪式空间才能显现。
这种记忆建构方式暴露出现代亲情的本质困境:我们对父母的认知,不容易在他们的职业身份与家庭角色之间取得平衡。在文末,当作者承认「我才真正发现我所说的,并不是一个亲人的经歷,而是一个生命永远的执着」时,有了实质的觉醒:父爱的存在需超出传统伦理框架,在更广阔的维度中被理解。
当戏院终将被数位洪流吞没,父亲的执着显现出先知般的悲剧性。这对父子的故事,既是个体命运的缩影,也是世代精神困境的寓言。那些被重复了五十年的带位动作,那些在黑暗中悄然传递的体温,最终在记忆的银幕上融合为存在主义的坚定回应:爱的本质,或许就是允许对方成为自己命运的偏执狂。当儿子最终接过父亲的手电筒,在人工製造的黑暗裡重现带位仪式时,这种跨越生死的角色扮演,成就了父子间最动人的情感救赎——我们终究要用父母的逻辑,才能读懂他们爱的密码。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着凄美背景的温情故事。「更深愁对月,怜此薄命人」这句崑曲唱词的点题,似乎过于悲凉!父亲的戏院人生犹如本雅明笔下的「灵光」残片,在数位时代的暗夜中闪烁微光。当我们理解这种「重复即永恆」的存在智慧,方能真正读懂文末的终极隐喻:那些被父亲「吻遍的菲林」,实为机械时代最动人的情书——用五十年的时光长度,在齿孔间镌刻永恆的剎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