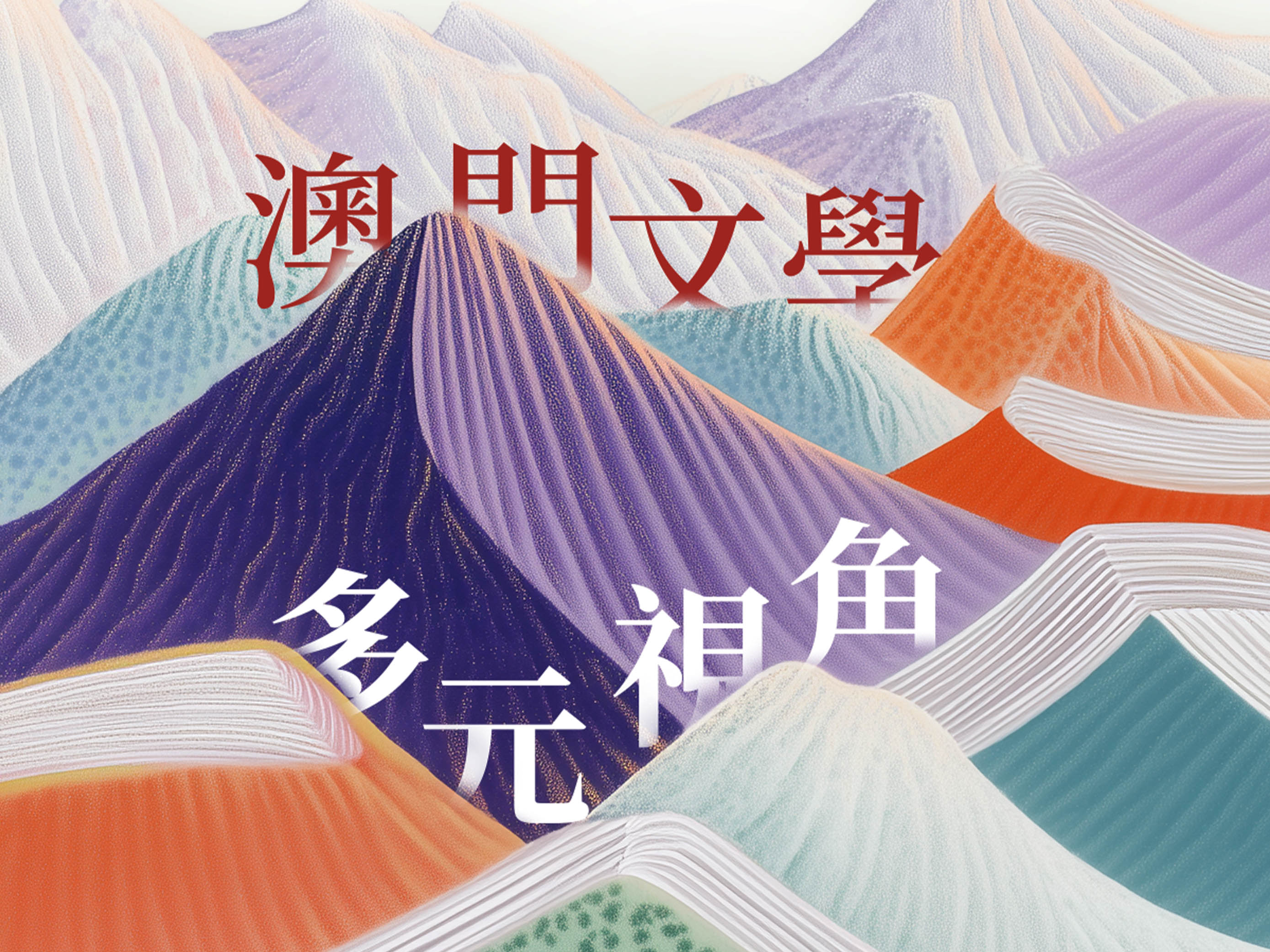《多多》,第八届纪念李鹏翥文学奖诗歌组首奖,作者诗子。
小城残旧的工厦单位,平凡的週六午後,一个平凡的生命悄然离场。读罢《多多》,彷佛在冰天雪地裡喝了一杯凉水,恍惚间,又彷佛听到神秘四维空间的召唤。诗子选取平凡的城市生活切面,以极具张力的语言和细腻的情感描绘了生命离别的时刻,同时又昇华到对光与存在、死亡与永恆的思考。五节诗犹如五级阶梯,交缠迴旋上升,从具体到抽象,从个体到宇宙,从私人情感到哲学思考,呈现出莫比乌斯环式的文本结构和多态疊加的诗意世界。
一、 结构:莫比乌斯环的对抗
诗作开篇即将读者拉入设定的静止背景:“三月的某个星期六”“下午”(时间),“温热的天气”“马路旁边”“无风”(地点、天气),压抑的“荒芜”带来的紧张被“随意生长”的“杂草”和“随意呼吸”的“万物”轻轻消解,但随即被“除了你”重新关闭呼吸通道,令人气闷——诗子“三月”的“残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艾略特的“四月”啊!(《荒原》:“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她轻巧地排下几个词语,便控制住你呼吸的节奏:“生长”(动)-“无风”(静)-“呼吸”(动)-“除了你”(静),仿佛起伏的胸膛,又彷佛临终的心电图,眼睛滑过的同时,你的呼吸也被同步了。诗人在第一节末句突兀而状似残忍地关闭了生命的阀门,却从门缝底下流出了一条悲伤的河。
残忍,当然不是诗人的本心,真正残忍的,是“无风”“无浪”的天地自然。彷佛为了对抗綫性时间,诗子煞费苦心地为“你”摺疊时空,以“三月星期六下午”为锚点,新造了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莫比乌斯时空环:首节以荒芜的街景铺开现实,中间在“復活藤篮”(第三节)的微观视角与“离岛”“黑炉”(第四节)的宏观观察之间腾挪,又在“残旧工厦裡的一个小单位”和“天堂”(第二节)及“卑第围”的“亮白角落”与“离岛”“黑炉”(第四节)之间构建出虚实交错的双重空间。如此的记忆编码方式,仿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非自主记忆”(或作“非意愿记忆”,mémoire involontaire)——葬礼现场被编织为多重时空的虫洞,既像挂毯一样紧密,同时正反两面包含不同花纹,彷佛记忆的电子同时通过两条路径抵达终点那般,也象徵与记忆同在的是遗忘,又或者说,与“现在”相对的是“永恆”。
《多多》呈现出时空交织的迴旋体形态,但是,它的拓扑学闭环轨迹运行最终却并非回到原点。诗子巧妙构造的翻转时空同时又让人想起但丁《神曲》的三界漫游,只不过是在工业化场景中完成现代性改写——“残旧工厦”取代“地狱阶梯”,“復活藤篮”隐喻“净化摇篮”,最终以“光”的辩证抵达“天堂”的终极隐喻,形成“现实-超验-死亡-哲思”的行进层次。莫比乌斯环没有起点和终点,克莱因瓶也无分内外。在这一场神圣的哀悼仪式中,“你”和“我”在“光”的映射中,完成了自性和他性的合一。
二、意象:诗意的多态疊加
《多多》将神学教义进行工业化重铸,从而达到某程度的神话解构:“天堂”被压缩至“残旧工厦裡的一个小单位”,“復活”被囚禁于“藤篮”。“残旧工厦裡的一个小单位”与“天堂”看似矛盾,却蕴含了诗人对世俗与超然的反思,二者的糅合,象徵诗人对崇高传统的反叛。携带民俗记忆的“藤篮”与“工厦”形成文明断裂,“残旧”亦意味着工业文明的衰败,“復活”神话在钢筋混凝土中异化为存在主义寓言。结尾“话不多的人”,让人想起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简单綫条勾勒出的几何形天使睁眼张口,露出稀疏的牙齿,面向过去,振翅欲走还留:巨灾(Katasthrophe)留下的砾碎堆成废墟,要黏好碎片、復苏亡者吗?风暴从乐土(Paradise)卷来,强扭天使转向未来,碎片自废墟往天堂(Himmel)漫延——这就是进步。“新天使”化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歷史的天使”,通过“话不多的人”,以神谕式宣言终结所有的佔有话语,助“散落在光的领地”的“我”进行自我补救、重塑和完满,实现对“我”的终极救赎。与此同时,诗子将“人间思念”“延续”向“是名词也是终点”以及“寄望的起点”的“天堂”,完成了对“残旧”现实的精神超越。
这一段“超越”之旅,“光”对“被火化”的生命碎片和“人间思念”碎片的射影变换是关键。“多多”或许是诗子心爱的宠物猫。诗子将零的事件点——多多之死,具象化成“你的眼缝中”的“光”,并以之作为观察坐标系之原点,与“黑炉内/燃烧”的“光"及後续“在谁的瞇缝中”形成的“光的领地”,共同在闵可夫斯基时空图中形成系列事件的类光间隔——这裡,或可称之之为“多多光锥”。当哀伤的“我”试图解构自我并将碎片“散落在光的领地”,却在不经意闲构建出洛伦兹变换下的参照系:生者“我”与逝者“你”的世界线在“多多光锥”的表面相遇,印证了“光不佔有任何事物”的伦理宣言——量子纠缠中的超距作用恰是诗中“你”“我”之非佔有性联结的物理隐喻。
完成对生与死的几何学光锥投影后,诗人继续在意象上疊加诗学意义上的真实性悖论:“无风”与“随意呼吸”的矛盾共在率先抛出“有”与“无”的存在命题。将静态“名词”“天堂”置放于“起点”与“终点”之间极限拉扯,在拉扯的过程中完成从空间概念到时间过程的转化。“空气不空”通过物理性质层面的否定指向“我”之情感密度的超载。用“燃烧”作为“生命”的提喻(Synecdoche),同时指向“发光发热”的生和“终被火化”的死。“光不佔有”则揭示了主观意愿(“企图让光,佔据我”)和客观现实的遥远距离。诗子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否定词“不”将日常语言辖域撕裂(“空气不空”),迫使词语在向哲学与科学乃至宗教交界处奔逃的过程中,衍生出诗意的张力,完美实践了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 “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策略。这种精心设计的语言实验,亦可看作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最高虚构”理论(Supreme Fiction)的当代实践:以诗为载体,向读者提供认知的临界体验。
《多多》呈现出来的诗意疊加态当然不限于此。“杂草”“马路”“残旧工厦”“卑第围”“离岛”构成艾略特式的城市意象拼贴的同时又带有辛波斯卡(Szymborska)式的对日常事物的现象学凝视。时间的截断面——“三月的某个星期六下午”承载了当代集体无意识中的断裂感。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徵“并置”(Juxtaposition)在诗中更是俯拾即是:“工厦”的“残旧”与“天堂”的纯净并置、“白”与“黑”并置,“黑炉”的冰冷静止和炉火的高温“燃烧”并置,“復活”与死亡并置,“光”的佔据与不佔据并置。这些意象如量子般相互纠缠,形成非逻辑的“超现实关联”。尤其精彩的是,“卑第围的一个亮白角落”的“我”和“在离岛/在城市另一端的黑炉内/燃烧”的“火”,有意製造的空间分裂却抵挡不住生者与逝者之间的情感隧穿。精心选择的意象群自此形成美妙的召唤结构,给思念创造了足够的绵延空间。
三、“光”的幽灵:零度写作下燃烧的火
《多多》对时空的精心折疊,不是简单的折千纸鹤式的祈祷,而是潘奈洛佩(Penélopê)手中织布机上的寿衣布,白天织、晚上拆,日日如是,以此拒绝求婚者们的纠缠,等待丈夫战神奥德修(Odysséus)的归来,——是包含着深情的守候和期待的。不是吗?诗子并没有在诗中提及“爱”和“伤”或者 “死亡”,她像一个冷静的巧手匠,将对多多的感情,用多重方式,编成一首“ai”诗——哀,与爱同在。
《多多》首先是沉默的。从杂草丛生的“马路”到“残旧工厦裡的一个小单位”,从地面到天空,一切都是“安安静静”的。直到第二节末尾,诗人终于忍不住了,她不再沉默,她凝望多多,轻轻説道“请多多休息/请多多,保重”,但旋即又恢復沉默。躺在“復活藤篮裡”的“你”,“走进卑第围的一个亮白角落”的“我”,“黑炉内燃烧”的“火”,默契地保持静默,直至结尾“话不多的人”宣判结局。当然,《多多》的沉默是轻盈的,自然不能与保罗.策兰(Paul Celan)之玄铁一般的“沉默”相比。但策兰诗歌中光的创伤性隐喻(如《死亡赋格》中“黑牛奶”与光的对峙)或许啓发了“眼缝中”的“光”与“光不佔有”的辩证。表面的沉默往往意味着内心的喧嚣,诗子用“空气不空”的悖论修辞,将语言推向沉默美学的边缘。我们要做的是,在“光”的在场与缺席之间填补意义,正如策兰的诗歌要求读者参与语言的修復。
罗兰.巴特提出的“零度写作”在诗中体现为克制的语调。诗人冷眼看着“眼睑,盖住了黑眼珠”,她的脸似乎是淡漠的,但她拒绝使用“死”字。她用“除了你”“休息”“安安静静”“眼缝中/有光”来替代,为冰冷的死亡事件披上了温暖的“小被子”。尽管她“走进卑第围的一个亮白角落”,选择远离告别现场(“火,在离岛/在城市另一端的黑炉内/燃烧),但身体的刻意隔离并不能割裂情感的深度粘连。多多的离去,“如婴儿,盖好了小被子”——在诗子的世界裡,死亡不是终结。多多仿如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之七)中那些“始终在寻求尘世”的“未成熟的魂灵”,它生命的“终点”“也是/寄望的起点”。透过“你的眼缝中” 的“光”,诗子和多多之间开啓了情感的量子隧穿。此时的哀悼仪式已昇华为存在的凝视。
“光”作为存在的显现,自然而然成为全诗展开形而上追问的中心。从“妳的眼缝中”直面死亡的、残存的微光,到“我把自己散落在光的领地”的主体性消融,最终抵达“光不佔有”的虚拟彼岸,“光”的辩证过程暗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路径——当“燃烧”化身薛定谔的猫,引发“发光发热”态和“火化”态的疊加存在,存在的虚无面纱瞬时被“光”之利剑一把挑开:作为“存在”(Sein)的显现的“光”,无法像“存在者”(Seiende)一样,成为被佔有的客体。而“我”企图被“光”殖民的献祭冲动,同时道出了人类对意义佔有的永恆焦虑(里尔克:“我喜欢意义,我愿意留在意义之下。”)。
诗子在末尾说,“光不佔有任何事物”,是的,光不佔有,也不被佔有。哀悼,不是逝者对生者记忆的编码和佔据,也不是生者对逝者的企图永恆囚禁。《多多》对多多的哀悼,是诗子对多多最深沉的守护。当多多在火化炉中湮灭,又在眼缝之光中永存,它就不需要再逃避谁的掌控了。哀悼,化作一道光,成就幽灵性的在场。
四、结语
诗子给我们织了一张存在之网。《多多》的价值,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熔铸成光的稜镜——当我们凝视那些被折射的七彩幻象,或许能窥见永恆虚无中剎那真实的、那一点诗意的星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