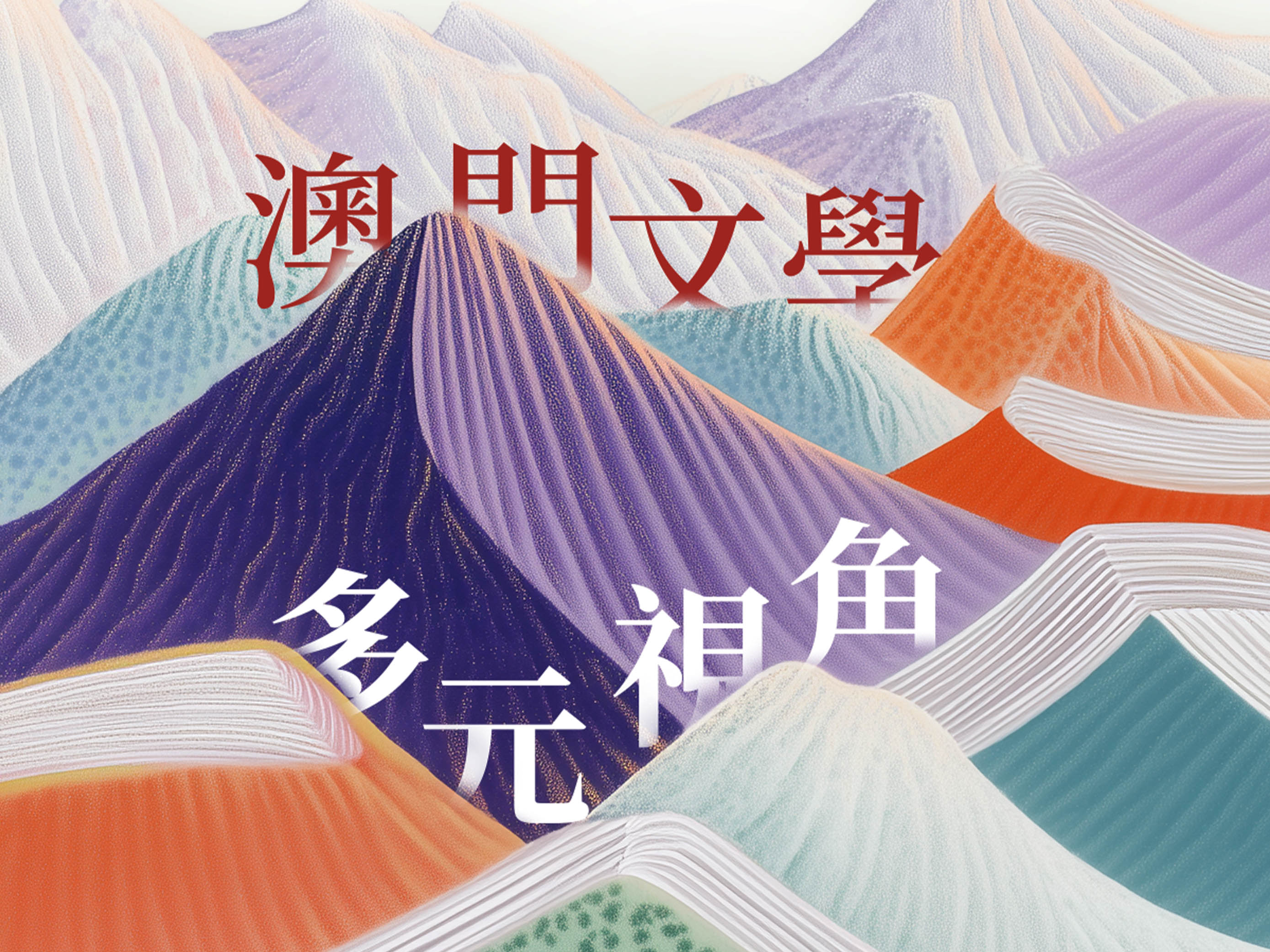《多多》,第八屆紀念李鵬翥文學獎詩歌組首獎,作者詩子。
小城殘舊的工廈單位,平凡的週六午後,一個平凡的生命悄然離場。讀罷《多多》,彷佛在冰天雪地裡喝了一杯涼水,恍惚間,又彷佛聽到神秘四維空間的召喚。詩子選取平凡的城市生活切面,以極具張力的語言和細膩的情感描繪了生命離別的時刻,同時又昇華到對光與存在、死亡與永恆的思考。五節詩猶如五級階梯,交纏迴旋上升,從具體到抽象,從個體到宇宙,從私人情感到哲學思考,呈現出莫比烏斯環式的文本結構和多態疊加的詩意世界。
一、 結構:莫比烏斯環的對抗
詩作開篇即將讀者拉入設定的靜止背景:“三月的某個星期六”“下午”(時間),“溫熱的天氣”“馬路旁邊”“無風”(地點、天氣),壓抑的“荒蕪”帶來的緊張被“隨意生長”的“雜草”和“隨意呼吸”的“萬物”輕輕消解,但隨即被“除了你”重新關閉呼吸通道,令人氣悶——詩子“三月”的“殘忍”程度,一點也不亞於艾略特的“四月”啊!(《荒原》:“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她輕巧地排下幾個詞語,便控制住你呼吸的節奏:“生長”(動)-“無風”(靜)-“呼吸”(動)-“除了你”(靜),仿佛起伏的胸膛,又彷佛臨終的心電圖,眼睛滑過的同時,你的呼吸也被同步了。詩人在第一節末句突兀而狀似殘忍地關閉了生命的閥門,卻從門縫底下流出了一條悲傷的河。
殘忍,當然不是詩人的本心,真正殘忍的,是“無風”“無浪”的天地自然。彷佛為了對抗綫性時間,詩子煞費苦心地為“你”摺疊時空,以“三月星期六下午”為錨點,新造了一個敘事學意義上的莫比烏斯時空環:首節以荒蕪的街景鋪開現實,中間在“復活藤籃”(第三節)的微觀視角與“離島”“黑爐”(第四節)的宏觀觀察之間騰挪,又在“殘舊工廈裡的一個小單位”和“天堂”(第二節)及“卑第圍”的“亮白角落”與“離島”“黑爐”(第四節)之間構建出虛實交錯的雙重空間。如此的記憶編碼方式,仿如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非自主記憶”(或作“非意願記憶”,mémoire involontaire)——葬禮現場被編織為多重時空的蟲洞,既像挂毯一樣緊密,同時正反兩面包含不同花紋,彷佛記憶的電子同時通過兩條路徑抵達終點那般,也象徵與記憶同在的是遺忘,又或者說,與“現在”相對的是“永恆”。
《多多》呈現出時空交織的迴旋體形態,但是,它的拓撲學閉環軌跡運行最終卻並非回到原點。詩子巧妙構造的翻轉時空同時又讓人想起但丁《神曲》的三界漫遊,只不過是在工業化場景中完成現代性改寫——“殘舊工廈”取代“地獄階梯”,“復活藤籃”隱喻“淨化搖籃”,最終以“光”的辯證抵達“天堂”的終極隱喻,形成“現實-超驗-死亡-哲思”的行進層次。莫比烏斯環沒有起點和終點,克萊因瓶也無分內外。在這一場神聖的哀悼儀式中,“你”和“我”在“光”的映射中,完成了自性和他性的合一。
二、意象:詩意的多態疊加
《多多》將神學教義進行工業化重鑄,從而達到某程度的神話解構:“天堂”被壓縮至“殘舊工廈裡的一個小單位”,“復活”被囚禁於“藤籃”。“殘舊工廈裡的一個小單位”與“天堂”看似矛盾,卻蘊含了詩人對世俗與超然的反思,二者的糅合,象徵詩人對崇高傳統的反叛。携帶民俗記憶的“藤籃”與“工廈”形成文明斷裂,“殘舊”亦意味著工業文明的衰敗,“復活”神話在鋼筋混凝土中異化為存在主義寓言。結尾“話不多的人”,讓人想起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簡單綫條勾勒出的幾何形天使睜眼張口,露出稀疏的牙齒,面向過去,振翅欲走還留:巨灾(Katasthrophe)留下的礫碎堆成廢墟,要黏好碎片、復蘇亡者嗎?風暴從樂土(Paradise)卷來,強扭天使轉向未來,碎片自廢墟往天堂(Himmel)漫延——這就是進步。“新天使”化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歷史的天使”,通過“話不多的人”,以神諭式宣言終結所有的佔有話語,助“散落在光的領地”的“我”進行自我補救、重塑和完滿,實現對“我”的終極救贖。與此同時,詩子將“人間思念”“延續”向“是名詞也是終點”以及“寄望的起點”的“天堂”,完成了對“殘舊”現實的精神超越。
這一段“超越”之旅,“光”對“被火化”的生命碎片和“人間思念”碎片的射影變換是關鍵。“多多”或許是詩子心愛的寵物貓。詩子將零的事件點——多多之死,具象化成“你的眼縫中”的“光”,並以之作為觀察坐標系之原點,與“黑爐內/燃燒”的“光"及後續“在誰的瞇縫中”形成的“光的領地”,共同在閔可夫斯基時空圖中形成系列事件的類光間隔——這裡,或可稱之之為“多多光錐”。當哀傷的“我”試圖解構自我並將碎片“散落在光的領地”,卻在不經意閒構建出洛倫茲變換下的參照系:生者“我”與逝者“你”的世界線在“多多光錐”的表面相遇,印證了“光不佔有任何事物”的倫理宣言——量子糾纏中的超距作用恰是詩中“你”“我”之非佔有性聯結的物理隱喻。
完成對生與死的幾何學光錐投影后,詩人繼續在意象上疊加詩學意義上的真實性悖論:“無風”與“隨意呼吸”的矛盾共在率先拋出“有”與“無”的存在命題。將靜態“名詞”“天堂”置放於“起點”與“終點”之間極限拉扯,在拉扯的過程中完成從空間概念到時間過程的轉化。“空氣不空”通過物理性質層面的否定指向“我”之情感密度的超載。用“燃燒”作為“生命”的提喻(Synecdoche),同時指向“發光發熱”的生和“終被火化”的死。“光不佔有”則揭示了主觀意願(“企圖讓光,佔據我”)和客觀現實的遙遠距離。詩子的高明之處在於,利用否定詞“不”將日常語言轄域撕裂(“空氣不空”),迫使詞語在向哲學與科學乃至宗教交界處奔逃的過程中,衍生出詩意的張力,完美實踐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 “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策略。這種精心設計的語言實驗,亦可看作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最高虛構”理論(Supreme Fiction)的當代實踐:以詩為載體,向讀者提供認知的臨界體驗。
《多多》呈現出來的詩意疊加態當然不限於此。“雜草”“馬路”“殘舊工廈”“卑第圍”“離島”構成艾略特式的城市意象拼貼的同時又帶有辛波斯卡(Szymborska)式的對日常事物的現象學凝視。時間的截斷面——“三月的某個星期六下午”承載了當代集體無意識中的斷裂感。現代主義的核心特徵“並置”(Juxtaposition)在詩中更是俯拾即是:“工廈”的“殘舊”與“天堂”的純淨並置、“白”與“黑”並置,“黑爐”的冰冷靜止和爐火的高溫“燃燒”並置,“復活”與死亡並置,“光”的佔據與不佔據並置。這些意象如量子般相互糾纏,形成非邏輯的“超現實關聯”。尤其精彩的是,“卑第圍的一個亮白角落”的“我”和“在離島/在城市另一端的黑爐內/燃燒”的“火”,有意製造的空間分裂卻抵擋不住生者與逝者之間的情感隧穿。精心選擇的意象群自此形成美妙的召喚結構,給思念創造了足夠的綿延空間。
三、“光”的幽靈:零度寫作下燃燒的火
《多多》對時空的精心折疊,不是簡單的折千紙鶴式的祈禱,而是潘奈洛佩(Penélopê)手中織布機上的壽衣布,白天織、晚上拆,日日如是,以此拒絕求婚者們的糾纏,等待丈夫戰神奥德修(Odysséus)的歸來,——是包含著深情的守候和期待的。不是嗎?詩子並沒有在詩中提及“愛”和“傷”或者 “死亡”,她像一個冷靜的巧手匠,將對多多的感情,用多重方式,編成一首“ai”詩——哀,與愛同在。
《多多》首先是沉默的。從雜草叢生的“馬路”到“殘舊工廈裡的一個小單位”,從地面到天空,一切都是“安安靜靜”的。直到第二節末尾,詩人終於忍不住了,她不再沉默,她凝望多多,輕輕説道“請多多休息/請多多,保重”,但旋即又恢復沉默。躺在“復活藤籃裡”的“你”,“走進卑第圍的一個亮白角落”的“我”,“黑爐內燃燒”的“火”,默契地保持靜默,直至結尾“話不多的人”宣判結局。當然,《多多》的沉默是輕盈的,自然不能與保羅.策蘭(Paul Celan)之玄鐵一般的“沉默”相比。但策蘭詩歌中光的創傷性隱喻(如《死亡賦格》中“黑牛奶”與光的對峙)或許啓發了“眼縫中”的“光”與“光不佔有”的辯證。表面的沉默往往意味著內心的喧囂,詩子用“空氣不空”的悖論修辭,將語言推向沉默美學的邊緣。我們要做的是,在“光”的在場與缺席之間填補意義,正如策蘭的詩歌要求讀者參與語言的修復。
羅蘭.巴特提出的“零度寫作”在詩中體現為克制的語調。詩人冷眼看著“眼瞼,蓋住了黑眼珠”,她的臉似乎是淡漠的,但她拒絕使用“死”字。她用“除了你”“休息”“安安靜靜”“眼縫中/有光”來替代,為冰冷的死亡事件披上了溫暖的“小被子”。儘管她“走進卑第圍的一個亮白角落”,選擇遠離告別現場(“火,在離島/在城市另一端的黑爐內/燃燒),但身體的刻意隔離並不能割裂情感的深度粘連。多多的離去,“如嬰兒,蓋好了小被子”——在詩子的世界裡,死亡不是終結。多多仿如里爾克《杜伊諾哀歌》(之七)中那些“始終在尋求塵世”的“未成熟的魂灵”,它生命的“終點”“也是/寄望的起點”。透過“你的眼縫中” 的“光”,詩子和多多之間開啓了情感的量子隧穿。此時的哀悼儀式已昇華為存在的凝視。
“光”作為存在的顯現,自然而然成為全詩展開形而上追問的中心。從“妳的眼縫中”直面死亡的、殘存的微光,到“我把自己散落在光的領地”的主體性消融,最終抵達“光不佔有”的虛擬彼岸,“光”的辯證過程暗合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的哲學路徑——當“燃燒”化身薛定諤的貓,引發“發光發熱”態和“火化”態的疊加存在,存在的虛無面紗瞬時被“光”之利劍一把挑開:作為“存在”(Sein)的顯現的“光”,無法像“存在者”(Seiende)一樣,成為被佔有的客體。而“我”企圖被“光”殖民的獻祭衝動,同時道出了人類對意義佔有的永恆焦慮(里爾克:“我喜歡意義,我愿意留在意義之下。”)。
詩子在末尾說,“光不佔有任何事物”,是的,光不佔有,也不被佔有。哀悼,不是逝者對生者記憶的編碼和佔據,也不是生者對逝者的企圖永恆囚禁。《多多》對多多的哀悼,是詩子對多多最深沉的守護。當多多在火化爐中湮滅,又在眼縫之光中永存,它就不需要再逃避誰的掌控了。哀悼,化作一道光,成就幽靈性的在場。
四、結語
詩子給我們織了一張存在之網。《多多》的價值,不在於給出答案,而在於將現代人的精神困境熔鑄成光的稜鏡——當我們凝視那些被折射的七彩幻象,或許能窺見永恆虛無中剎那真實的、那一點詩意的星芒。